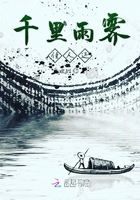西山的乱葬岗上,到处是些不知名的坟包,大大小小,随随便便的立着,新旧不一。坟里睡着的是已经归天的魂灵,有的是路过的风尘仆仆、无故染疾客死他乡的赶考书生,有的是走街串巷,机灵轻巧的货郎担,有的是喜欢在冬日里坐在墙根下晒太阳的老大爷;有些坟包上长满了不知名的野花,在这片迷茫的春风里轻轻摇曳;有的被路过的牲口、野兽翻过,尸骨暴露出来,有大小不一,参差不齐的啃咬痕迹,仔细看去,有的趾骨不过寸长,想来约么是个婴儿。人死如灯灭,不管生前如何繁华锦绣,再多的快意恩仇也不过落得个寂寥收场。在某个新立起的小坟包前,玖宁静静站着,这是喜婆婆的坟,她该伤心的,她想。可是纷扬的柳絮过处,玖宁灰褐色的衣角轻轻掀起,心里却只是一片空茫。
玖宁记忆的最初,是一片紫藤花架,温柔清丽的娘亲身着紫色衣袍,青丝翻飞,整个人似要融入那片深紫明紫浅紫之中,朱唇轻启,有软糯轻柔的声音含笑乘风而来,“小久宁啊小久宁,娘亲只盼着你一世长久安宁”。儒雅清俊的爹爹手执书卷,素青衫子的衣摆被风轻轻撩起,卷出俏皮不一的波浪来,读在兴头处,偶尔回过头,笑得温文尔雅,如沐春风;自己好像才只是三四岁的年纪吧,不知愁苦,不知将来……
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呢?后来,玖宁也不记得了,不知道是想不起来,还是不想想起来,反正是不记得了。如一场做的不够尽兴的黄粱美梦,有过欢愉,却终究只是幻梦一场,连余音也不会绕梁,便毫不留情的回到了昨夜那一阵漫不经心的穿堂而过的山风里。玖宁不是没想过问问喜婆婆,后来怎么样了呢?但是话每到嘴边,便像昨夜喝过的野菜汤一样,哧溜一下,便滚回了肚子里。
喜婆婆是一个和蔼慈祥的老人,一笑,脸上的皱纹便皱成了一朵菊花,直让跟她说话的人也觉得有无限兴味,心里欢喜热乎的像被阳光暖暖的晒着,时间一长,人家便把喜婆婆的本姓也忘了,就只是“喜婆婆,喜婆婆”的叫着,也没人觉着不妥,好像就应该这么叫似的。
喜婆婆也不是总是笑眯眯的,玖宁就有时捡着野菜,突然抬起头,就会看见喜婆婆神色莫辨的盯着自己,见她望过来,才微微笑将起来;有时候扫着院子,会突然听到喜婆婆的一声长叹;傍晚时分静静坐在门槛上,眼神虚无,空茫无依,似乎在看着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有看。
玖宁的家位于绿水村的小村子里,一座座山这么绵延下去,好像没有尽头,而其中两座山中间的平坦的地界,稀稀两两的矗立着几个茅草屋,而其中最东头的距离其他人家的较远一些的就是玖宁家,孤零零,俏生生的立在风中,就像那长在山间的飘摇茉莉,孤绝,飘零。这是夏日,从一座山包望过去,远处是望不到头的与天际连成一片的原野,灰扑扑的,玖宁常常想,那尽头是什么呢?思来想去,终是无果。在玖宁的所有可以开发的记忆里,饶是她绞尽了脑汁,也不过是一片虚无罢了。
不过,这些倒不是玖宁生活的重头戏,只是每天她做好晚饭,闲极无聊时,抱着围着她撒着欢子的隔壁二毛家的大黄随便想一想的,每当她看到一个佝偻蹒跚的身影远远的从山坡上下来,喜婆婆挎着篮子走进村子里,玖宁便欢喜的奔过去,大黄跟在她后面跑,喜婆婆笑将起来,这时村里家家户户正在做饭或者已经做好饭正等着当家归来们的女人孩子们就会听到清脆响亮的一声:“阿婆——”和着傍晚凉爽怡人的山风,缠缠绵绵,穿过山沟,一路奔腾而去,最后渺无踪迹。
喜婆婆最喜欢做的事是带着玖宁漫山遍野的挖野菜和草药,可入食,可卖,这是保证祖孙俩在这遍地饿殍的时节里活着的根本;其次就是在用过晚饭后,抱着小玖宁,坐在门槛上,摇啊摇,祖孙两望着像是被水洗过的月亮,听着此起彼伏的狗吠声,说着白日里没时间说的悄悄话:
有时是大黄又产了一窝小崽子,你想不想抱来一只养啊?抱来养当然是不可能的,祖孙两自己的温饱问题还没解决,哪里还养的起狗崽子?!也只是说着玩玩罢了;有时候是讲一些白日里见过哪些人,背着书袋、带着书童的书生,扛着榔头的庄稼汉子,坐着轿子、看不见衣着服饰和装扮的朱家老爷……说一说他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带着怎样的风尘,猜一猜他们形色匆匆,是要往哪里去?即将奔赴怎样的人生?这些本是寻常的事情,经过喜婆婆的嘴一说出来,便有了无限妙趣和意味,玖宁听得津津有味,偶尔也插两句嘴。
月亮渐渐高了,狗吠声也渐渐小了,只听得墙角下,草丛里一阵阵虫鸣一阵又一阵,高高低低,此起彼伏。皎洁而又干净的月光笔直地穿过破纱窗,直照的祖孙俩的小茅草屋里也亮亮堂堂,玖宁听的有些困了,小脑袋直点,喜婆婆便抱起玖宁,穿过小小的院子,边走边迷迷糊糊的说,“‘王’即是‘忘’,老爷既然给你改名‘玖宁’,往事种种,化作尘土。你也就都忘了吧。”
夜,深了。只余一枚朗月高高地挂在天际,高洁,茫远,又神秘莫测。
这是玖宁十二岁以前的生活,但从今日起,她将是一个人。春夏秋冬,只有她一个人。不是不害怕,可是想起之前喜婆婆颤抖着身躯日夜不间断剧烈的咳嗽,玖宁又觉得,这是一种解脱。她拍拍衣裳,站起身子,脚步未停,头也不回的往山下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