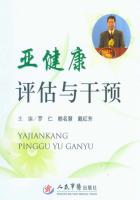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须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内时,当恻隐即恻隐,当羞恶即差恶。谁欺得你?谁瞒得你?见得端的后,常涵养,是甚次第。
勿无事生事。
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至哉!真圣人学也。
把捉二字不佳,不如说固执。
克己,三年克之,颜子又不是如今人之病要克,只是一些子未释然处。
要知尊德乐道,若某不知尊德乐道,亦被驱将去。
诸子百家,说得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处未是。佛老亦然。
邑中讲说,闻者无不感发。独朱益伯鹘突来问,答曰:
“益伯过求,以利心听,故所求在新奇玄妙。”
积思勉之功,旧习自除。
择善固执,人旧习多少,如何不固执得?
知非则本心即复。
人心只爱去泊着事,教他弃事时,如鹘孙失了树,更无住处。
既知自立,此心无事时,须要涵养,不可便去理会事。
如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圣人谓“贼夫人之子。”学而优则仕,盖未可也。初学者能完聚得几多精神,才一霍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样完养,故有许多精神难散。
予因随众略说些子闲话,先生少顷曰:“显道今知非否?”某答曰:“略知。”先生曰:“须要深知,略知不得。显道每常爱说闲话。”
学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爱事骨董。君子之道,淡而不厌。朋友之相资,须助其知所好者,若引其逐外,即非也。
人皆可以为尧舜。此性此道,与尧舜元不异,若其才则有不同。学者当量力度德。
初教董元息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闲说话,渐渐好,后被教授教解论语,却反坏了。
人不肯心闲无事,居天下之广居,须要去逐外,着一事,印一说,方有精神。
惟精惟一,须要如此涵养。
无事时,不可忘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老子为学、为道之说,非是。如某说,只云:“着是而云非,舍邪而适正。”
有道无道之人,有才无才与才之高下,为道之幸不幸,皆天也。
我无事时,只似一个全无知无能底人。及事至方出来,又却似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人。
朱济道说:“前尚勇决,无迟疑,做得事。后因见先生了,临事即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过惩艾,皆无好处。”先生曰:“请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阙。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当宽裕温柔时自然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时自然发强刚毅。”
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恶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济道是为善所害。
心不可汩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来无事,胡乱被事物牵将去。若是有精神,即时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坏了。
人不肯只如此,须要有个说话。今时朋友尽须要个说话去讲。
后生有甚事。但遇读书不晓便问,遇事物理会不得时便问,并与人商量,其他有甚事。
自家表里内外如一。
因说金溪苏知县,资质好,亦甚知尊敬。然只是与他说得大纲话,大紧要处说不得。何故?盖为他三四十年父兄师友之教,履历之事几多,今胸中自有主张了,如何掇动得他?须是一切掇动划除了,方得如格。君亦须如此。然如吏部格法,如何动得他。
朱济道说:“临川从学之盛,亦可喜。”先生曰:“某岂不爱人人能自立,人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立乎其大者,而小者弗能夺。然岂能保任得朝日许多人在此相处?
一日新教授堂试,许多人皆往,只是被势驱得如此。若如今去了科举,用乡举里选法,便不如此。如某却爱人试也好,不试也好,得也好,不得也好。今如何得人尽如此?某所以忧之,过于济道。所悯小民被官吏苦者,以彼所病者在形,某之所忧人之所病者在心。”
与济道言:“风俗驱人之甚,如人心不明,如何作得主宰。吾人正当障百川而东之。”
先生曰:“某闲说话皆有落着处,若无谓闲说话,是谓不敬。”
某与济道同事,济道亦有不喜某处,以某见众人说好,某说不好,众人说不好,某解取之。
某与人理会事,便是格君心之非事。
举徐子宜云:“与晦庵月馀说话,都不讨落着,与先生说话,一句即讨落着。”
说济道滞形泥迹,不能识人,被人瞒。
济道问:“智者术之原,是否?”曰:“不是,伏羲画卦,文王重之,孔子系之,天下之理,无一违者,圣人无不照烛,此智也,岂是术?”因说:“旧曾与一人处事,后皆效。”彼云:
“察见渊鱼不祥,如何?”曰:“我这里制于未乱,保于未危,反祸为福,而彼为之者,不知如何为不祥?”
因举许昌朝集朱吕学规,在金溪教学,一册,月令人一观,固好,然亦未是。某平时未尝立学规,但常就本上理会,有本自然有末。若全去末上理会,非惟无益。今既于本上有所知,可略略地顺风吹火,随时建立,但莫去起炉作灶。
做得工夫实,则所说即实事,不话闲话,所指人病即实病。因举午间一人问虏使善两国讲和。先生因赞叹不用兵全得几多生灵,是好。然吾人皆士人,曾读春秋,知中国夷狄之辨。二圣之雠,岂可不复?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今吾人高居无事,优游以食,亦可为耻,乃怀安非怀义也。此皆是实理实说。
事外无道,道外无事。皋陶求禹言,禹只举治水所行之事,外此无事。禹优入圣域,不是不能言,然须以归之皋陶。
如疑知人之类,必假皋陶言之。
显仲问云:“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气禀清浊不同,只自完养,不逐物,即随清明,才一逐物,便昏眩了。显仲好悬断,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后随起来,又剥落,又清明,须是剥落得净尽方是。”
人心有消杀不得处,便是私意,便去引文牵义,牵枝引蔓,牵今引古,为证为靠。
既无病时好后书,但莫去引起来。
慥侄问:“乍宽乍紧,乍明乍昏如何?”曰:“不要紧,但莫懈怠。紧便不是,宽便;昏便不是,明便是。今日十件昏,明日九件,后日又只八件,便是进。”
语显仲云:“风恬浪静中,滋味深长。人资性长短虽不同,然同进一步则皆失,同退一步则皆得。”
问傅季鲁:“如何而通?如何而塞?”因曰:“某明时直是明,只是懈怠时即塞。若长鞭策,不懈怠,岂解有塞?然某才遇塞时,即不少安,即求出。若更藉朋友切磋求出,亦钝甚矣,所以淹没人。只朋友说闲话之类,亦能淹人。某适被显仲说闲话,某亦随流,不长进亦甚。然通时说事亦通,塞时皆塞。”
写字须一点是一点,一画是一画,不可苟。
彘鸡终日萦萦,无超然之意。须是一刀两断,何故萦萦如此?萦萦底讨个甚么?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今有难说处,不近前来底又有病,近前来底又有病。世俗情欲底人病却不妨,只指教他去彼就此。最是于道理中鹘突不分明人难理会。某平生怕此等人,世俗之过却不怕。
旧横截人太甚,如截周成之后,当不得无成。今皆不然,以次第进之。有大力量者,然后足以当其横截,即有出路。
教小儿,须发其自重之意。
予问能辩朱事。曰:“如何辩?”予曰:“不得受用。”曰:
“如此说便不得,彼亦可受用,只是信此心未及。”又曰:“只今明白时,便不须更推如何如何。”又曰:“凡事只过了,更不须滞滞泥泥。子渊却不如此,过了便了,无凝滞。”
区处得多少事,并应对人,手中亦读得书。
问:“二兄恐不知先生学问旨脉?”曰:“固是前日亦尝与朱济道说,须是自克却,方见得自家旧相信时亦只是虚信,不是实得见。”
我只是不说一,若说一,公便爱。平常看人说甚事,只是随他说,却只似个东说西说底人。我不说一,杨敬仲说一,尝与敬仲说箴他。
凡事莫如此滞滞泥泥,某平生于此有长,都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会一事时,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个闲闲散散全不理会事底人,不陷事中。
详道如昨日言定夫时,宏大磊落。常常如此时好,但莫被枝叶累倒了。须是工夫孜孜不懈乃得,若稍懈,旧习又来。
君子之道,淡而不厌。淡味长,有滋味便是欲。人不爱淡,却只爱闹热。人须要用不肯不用,须要为不肯不为。盖器有大小,有大大器底人自别。
算稳底人好,然又无病生病。勇往底人好,然又一概去了。然勇往底人较好,算稳底人有难救者。
定夫举禅说:“正人说邪说,邪说亦是正,邪人说正说,正说亦是邪。”先生曰:“此邪说也。正则皆正,邪则皆邪,正人岂有邪说?邪人岂有正说?此儒释之分也。”
古人朴实头,明播种者主播种,明乐者主乐,欲学者却学他,然长者为主。又其为主者自为主,其为副者自为副,一切皆有一定,不易不争。
宿无灵骨,在师友处有所闻,又不践履去,是谓无灵骨。
又云:“人皆可以为尧舜,谓无灵骨,是谓厚诬。”
后生随身规矩不可失。
道可谓尊,可谓重,可谓明,可谓高,可谓大。人却不自重,才有毫发恣纵,便是私欲,与此全不相似。
法语正如雷阳,巽语正如风阴。人能于法语有省时好,于巽语有省,未得其正,须思绎。诗雅、正、变风,便是巽意,离骚又其次也。变风无骚意,此又是屈原立此,出于有所碍,不得已。后世作诗雅,不得只学骚。
兵书邪说。道塞乎天地,以正伐邪,何用此。须别邪正。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此理塞宇宙,如何由人杜撰得?文王敬忌,若不知此,敬忌个甚么?
见季尉,因说:“大率人多为举业所坏。渠建宁人,尤溺于此。取人当先行义,考试当先理致,毋以举业之靡者为上。”
大丈夫事岂当儿戏?
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
四端皆我固有,全无增添。
说本朝官制,蔡元通所论乱道。
江泰之问:“某每惩忿窒欲,求其放心,然能暂而不能久。请教。”答曰:“但惩忿窒欲,未是学问事。便惩窒得全无后,也未是学。学者须是明理,须是知学,然后说得惩窒。
知学后惩窒,与常人惩窒不同。常人惩窒只是就事就未。”
孟子言学问之道求放心,是发明当时人。当时未有此说,便说得,孟子既说了,下面更注脚,便不得。
今上重明节九月四日早,先生就精舍庭前,朱衣象笏,向北四拜,归精舍坐,四拜。问之,答曰:“必有所尊,非有已也。太守上任拜厅。”
学者大率有四样:一、虽知学路,而恣情纵欲,不肯为。
一畏其事大且难而不为;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谓能知。
学能变化气质。
大人凝然不动,不如此,小家相。
先生云:“某每见人,一见即知其是不是,后又疑其恐不然,最后终不出初一见。”
道塞天地,人以自私之身与道不相入。人能退步自省,自然相入。唐虞三代教化行,习俗美,人无由自私得。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今都相背了,说不得。
高底人不取物,下人取物,粘于物。
资禀好底人阔大,不小家相,不造作,闲引惹他都不起不动,自然与道相近。资禀好底人,须见一面,自然识取,资禀与道相近。资禀不好底人,自与道相远,却去锻炼。
东坡论嗣征甚好,自五子之歌推来。顾命陈设,是因成王即位,流言所致,此召公之非不任道,流俗之情也。周之道微,此其一也。又“尔有嘉谋嘉猷,则人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此二也。
旧尝通张于湖书于建康,误解了中庸,谓“魏公能致广大而不能尽精微,极高明而不能道中庸”,乃成两截去了。
又尝作高祖无可无不可论,误解了书,谓“人心,人伪也;道心,天理也”,非是。人心,只是说大凡人之心。惟微,是精微,才粗便不精微,谓人欲天理,非是。人亦有善有恶,天亦有善有恶,日月蚀、恶星之类。岂可以善皆归之天,恶皆归之人。此说出于乐记,此说不是圣人之言。
与小后生说话,虽极高极微,无不听得,与一辈老成说便不然。以此见道无巧,只是那心不平底人揣度便失了。
学者须是打叠田地净洁,然后令他奋发植立。若田地不净洁。则奋发植立不得。古人为学即“读书然后为学”可见。然田地不净洁,亦读书不得。若读书,则是假寇兵,资盗粮。
几所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晏然太平,殊无一事。然却有说擒搦人不下,不能立事,却要有理会处。某于显道,恐不能久处此间。且今涵养大处,如此样处未敢发。然某皆是逐事逐物考究练磨,积日累月,以至如今,不是自会,亦不是别有一窍子,亦不是等闲理会,一理会便会。但是理会与他人别。某从来勤理会,长兄每四更一点起时,只见某在看书,或检书,或默坐。常说与子娃,以为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某懒,不曾去理会,好笑。
侍登鬼谷山,先生行泥涂二三十里。云:“平日极惜精力,不轻用,以留有用处,所以如今如是健。”诸人皆因不堪。
观山,云:“佳处草木皆异,无俗物,观此亦可知学。”
天地人之才等耳,人岂可轻?人字又岂可轻?有中说无,无中说有之类,非儒说。
因提公昨晚所论事,只是胜心。风平浪静时,都不如此。
先生说数、说揲蓍,云:“着法后人皆误了,吾得之矣。”
一行数妙甚,聪明之极,吾甚服之,却自僧中出。僧持世有历法八卷。
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夫权皆在我,若在物,即为物役矣。
举柳文乎、欤、邪之类,说乎、欤是疑,又是赞叹。“不亦说乎”是赞叹,“其诸异乎人之求之欤”是赞叹,孟子杞柳章一欤、一也,皆疑。
我说一贯,彼亦说一贯,只是不然。天秩、天叙、天命、天讨,皆是实理,彼岂有此?
后生全无所知底,似全无知,一与说却透得。为他中虚无事。彼有这般意思底,一切被这些子隔了,全透不得,此虚妄最害人。
过、不及,有两种人。胸中无他,只一味懈怠沉埋底人,一向昏俗去,若起得他却好,只是难起,此属不及。若好妄作人,一切隔了,此校不好,此属过。人凝重阔大底好,轻薄小相底不好。
槐云:“着意重便惊疑。”答:“有所重便不得。”举孟子勿忘勿助长。
优裕宽平,即所存多,思虑亦正。求索太过,即存少,思虑亦不正。
重滞者难得轻清,刊了又重。须是久在师侧,久久教他轻清去。若自重滞,如何轻清得人。
黄百七哥,今甚平夷闲雅,无营求,无造作,甚好。其资与其所习似不然,今却如此,非学力而何?
人之精爽,负于血气,其发露于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师良友剖剥,如何得去其浮伪,而归于真实?又如何得能自省、自觉、自剥落?
数即理也,人不明理,如何明数。
“神以知来,智以藏往。”神,蓍也,智,卦也,此是人一身之蓍。
某自来非由乎学,自然与一种人气相忤。才见一造作营求底人,便不喜,有一种冲然淡然底人,便使人喜,以至一样衰底人,心亦喜之。年来为不了事底,方习得稍不喜,见退淡底人,只一向起发他。
某从来不尚人起炉作灶,多尚平。
因观众人所为,亦多因他。然亦有心知其为非。下以为是,有二三年说破者。如此下为则已,一为必中。此虽非中,然与彼好生事不中底人相去悬绝。于事则如此多不为,至于文章,必某自为之。文章岂有太过人?只是得个恰好。
他人未有伦叙,便做得好,只是偶然。又云文章要锻炼。
诗小序,解诗者所为。“天下荡荡”,乃因“荡荡上帝”,序此尤谬可见者。
曾参高柴漆雕开之徒是不及之好者,曾是过之好者,师过商不及是过不及之不好者。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学者第一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此是第二。孔子志学便是志此,然须要有入处。周南召南便是入处。后生无志难说,此与秦誓其心休休一章相应。周南召南好善不厌,关瞧鹊巢皆然。人无好善之心便皆自私,有好善之心便无私,便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今人未必有他心,只是无志,便不好善。
乐正子好善,孟子喜而不寐,又不是私于乐正子?
因曾见一大鸡,凝然自重,不与小鸡同,因得关睢之意。
睢鸠在河之洲,幽闲自重,以此兴君子美人如此之美。
文以理为主,荀子于理有蔽,所以文不雅驯。
“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风是血脉,教是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