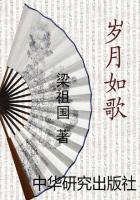当然了,我们当代一些作家的突出成就也推动了爱尔兰文学历史地位的发展。谢默斯·希尼,弗兰克·麦考特和罗迪·多伊尔引起了世人对爱尔兰作家的再度关注;还有一些作家如科姆·托伊宾,雨果·汉密尔顿和考勒姆·麦肯则属于很典型的爱尔兰传统作家,语言风格比较谨慎,叙述手法精妙,而他们也正在尝试写作很新的东西。
我认为爱尔兰作家很注重坚持传统风格,如讲故事的技巧、生动而丰富的通俗语言、对于形式技巧的追求,还有语言上的创新精神。(我并不是说他们都喜欢玩文字花样,只是有时文字过于简单就会有点别出心裁。)对于爱尔兰作家来说,写作的目的不在于仅仅讲述一个故事,而在于怎样讲述这个故事。我相信所有的读者对于这样一种在作者引领下开启的阅读之旅都会感兴趣的。
问:您是否会为文学附加任何社会功能?您个人会满足于读者喜爱您的作品吗?
答:我必须承认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非常天真和浪漫。我赞同济慈、雪莱和性手枪乐团(SexPistols)的说法,即艺术是为了改变世界。小说应该是美丽的,最好还要吸引入,但是对我而言,小说的创作绝对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所有艺术家或作家艺术创作的策略都要服务于这一改变的宗旨。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里,创造美丽实际上是一项政治作为。不管我们意愿如何,小说在客观上确实能改变世界。
问:能谈一下您对未来的写作计划吗?
答:我的计划就是继续写小说。我现在很少从事新闻写作了,也大大缩减了其它类型的文学创作,就是想争取更多的时间来专心写作小说。我现在正在构思一部新的小说。
(原载《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3期)
写作、政治以及《入土为安》
——哈罗德·品特访谈
戴从容译
时间:1996年12月6日
访谈者:米瑞亚·阿拉该(MireiaAragay),巴塞罗纳大学英语系教师拉蒙·西摩(RanionSimo),巴塞罗绅大学德语系教师我从未把抽象观念作为写作的出发点
阿拉该:写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品特:从很小的时候起,语言就一直让我极为兴奋。我开始写作是在十一或十二岁的时候。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就爱词语,那种兴奋感陪伴了我一生。看到纸上的词语,看到那张白纸以及想到可能写在上面的字,我现在依然会像过去一样兴奋。每张白纸都是一个未知的世界,而你将跃身其中。这非常具有挑战性。
阿拉该:1961年你与理查德·芬德雷特进行了一次对话,后来以《为自己写作》这一标题出版,在这次对话中,你说“我以处于某一特殊情境的人物作为出发点。我当然不是从哪个抽象的观念开始着笔。”这些年里,你的创造活动依然如此么?
品特:是的,我从未把抽象的观念作为写作的出发点。并不一定是特定的人物,或者不如说是特殊、具体的意象,无论视觉意象还是文字意象。
阿拉该:即便在你更近期的政治剧中,你也是这样着手写作的么?
品特:是的,即便在我更近期的明确的政治剧中。假如你要写一出戏剧,描写这些事态,你应该有一个创作冲动,这一冲动必须来自一个特定的形象。比女口,《饯行酒》(One for theR0ad)的起因,就是我脑海里出现一个坐在桌子上的男人,等侯着某人——他的受害者——走进房间。我觉得萨拉·贝克特剧场(Sala Beckett)巴塞罗纳的一个著名的实验剧场。将这个剧本演得非常出色。坐在桌上的男人这一意象就是触发了这部戏剧的那一具体事实。不是观念引出戏剧,而是那个男人的形象使戏剧得以展开。
西摩:在讨论你的创作活动的时候,你从未提到谋篇布局或者事先想好的结构,然而你的戏剧的形式极为精密。你能谈谈这两者如何在你的作品中共存的么?
品特:形式的构建是在创作戏剧的过程中进行的。我仍然发现我不得不构建非常精密的形式;这就是我诞生方式的一部分。我有冲动,然后我必须组织那一冲动,使它前后连贯。显然,连贯涉及到的是你如何塑造戏剧的语言和结构。我非常注意这个方面。两者就这样获得一致,一个是另一个的一部分。在戏剧的中段我遇到一只野兽,而作者必须抓住这只野兽。不过,顺便说一句,我喜欢野兽。如果没了野兽,也就根本一无所有了。
阿拉该:创作政治剧的时候,你是如何努力解决其中包含的美学的和道德的困难的?你如何避免向观众说教,变成某种宣传家?
品特:写这样的政治剧,如果你在开始写之前就已经知道了结尾,那么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我努力避免这一点,让戏剧保持新鲜,我希望我没在说教。我喜欢发现事态是怎么样的,然后让它发生。《宴会时间》(Party Time)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我最初有了一个想法,在某个城镇的一个非常优雅、富有的公寓里举行的一场宴会。我在写的时候,有个想法越来越清晰,即在外面的街道上,另一件事正在发生。渐渐地,另一点变得更加清晰,即街道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次镇压,事实上是由这个屋子里的人组织的。但是,屋子里的人自然从未讨论过这件事,只有一两次提到,一闪即逝。他们喝着香槟,吃着开胃薄饼,非常非常开心。他们知道一切进展顺利。换句话说,存在着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事实上根本不屑于讨论军队和警察的镇压行为,而他们是应对这些行为负责的。这一想法在写作的过程中浮现出来。我对此感到非常兴奋,因为它从来真正变得非常明确,但我想,又极为清晰。我相信不用努力告诉大家,它就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象。我相信在所有国家,都确实存在着掌握巨大权力的人,他们住在都会的公寓里,以许多非常微妙的方式——有时不那么微妙——事实上控制着发生在街道上的事情。但他们实际上不屑于谈论这件事,因为他们知道事情在发生,而且他们知道他们掌握着权力。这是一个权力如何运作的问题。
西摩:现在在欧洲,在剧作家以及所有与剧场有关的人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看法,即政治剧让人难以忍受。
品特:假如你说的政治卧是指处理现实世界的戏剧,而不是处理虚构的或幻想的世界的戏剧的话,那么如今,政治剧甚至比它在过去的时候还要重要。我们目前正处于可怕的低谷,一种深渊,因为大家以为政治无处不在。这是宣传机构的说法。而我不相信宣传。我相信,政治、我们的政治意识以及我们的政治智慧并非无处不在,因为假如这样的话,我们就真的注定毁灭了。我自己就不可能这样活着。我常常被告知,我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我肯定会自由。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我将保持头脑?和精神的独立,而且我认为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做到的。多数政治体系用这类含糊的话语说话,作为不同国家的公民,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对这种用语加以批判性的审视。当然,这意味着确实往往会变得很不受欢迎。不过,让欢迎见鬼去吧。
我们一生中的每一天,都是在这个暴力世界里长大的西摩:残暴和赤裸裸常常在你的政治剧中出现。讨论政治的时候,这两点是不是比较局限?
品特:我的戏剧不是政治讨论。它们是活生生的事。它们当然不是辩论。它们是暴力戏剧。暴力常常存在于我的戏剧中,从一开始就如此。《房间》(The Room)的结尾是一个突然的、完全无缘无故的暴力行为,一个男人把一个黑鬼踢死。那时我还相当年轻,不过回过头来看,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怪异或怪诞的事情。我们一生中的每一天,都是在这个暴力世界里长大的。
西摩:你在政治剧中塑造如此残暴、赤裸裸的形象,目的是什么?
品特:没有目的。我的戏剧中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我只是写,我是一个很直觉的作家。我没有算计好的目的或雄心,我仅仅发现我自己在写东西,而所写的东西有着自己的发展轨道。这条轨道上往往包含着这样或那样的暴力行为,因为这就是我生活的世界。你也如此。
阿拉该:在你的戏剧中,残暴和暴力常常与男性相连,而女人,尤其是在你20世纪60年代所写的戏剧中,则如谜一般,神秘莫测,她们拥有一种耐力,男性却似乎没有。
品特:她们在后期的戏剧中,也往往成为男性残暴的牺牲品。
阿拉该:你不觉得这是对男性和女性的一种相当脸谱化的看法么?
品特:可能。
阿拉该:你站在她们一边?
品特:事实上,我认为男性比女性更残暴。金斯利·阿米斯有一首蹩脚的两行诗,在诗中他说:“女性远远比男性美好/难怪我们喜欢她们。”我妻子认为这些诗行充满屈尊俯就的味道,它们确实如此,我完全同意。不过尽管如此,我绝对相信上帝在造女人的时候,精神状态要好得多。这并不等于说我对女性滥用感情。我觉得女人非常坚韧。不过如果你看看从创世之日起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真正的暴行都是由男人指使的。有时它们由女人来实施,这当然是事实。在德国集中营,女人从这个角度说干得很好,她们的确完成了那些把她们当作男人而要求她们做的事情。或者更确切地说,这并不重要。她们很难说是女人,她们不是男人,她们只是人,为她们的政府,她们的上帝服务。尽管如此,在我的戏剧中,女人总是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地成为一种我对其抱有某种感情的人,而我对男人没有这种感觉。
阿拉该:这是一种相当男性的视角,不是么?
品特:为什么不是呢?
幽默是我自身教养的一部分
阿拉该:在你的戏剧中有很多暴力,但就如你昨晚在萨拉?贝克特剧场提醒我们的,也有大量的幽默。幽默在你的戏剧中起着什么作用?它如何起作用?在暴行之中,幽默为什么出现?
品特:幽默非常神秘,我真的无法回答你的问题。幽默是我自身教养的一部分。我并不写那些我称作趣事的东西,但是它们中的一些确实让我发笑。我发现自己边写边笑,而且我注意到偶尔一两个人也在笑。
阿拉该:《入土为安》(Ashes to Ashes)在巴塞罗纳上演的第一个晚上,我听到观众在笑,这让我很惊异。我读剧本的时候,看不出它与任何特别有趣的事有关系。
品特:是的,在《入土为安》中有一些发笑的地方,不过我觉得它们止住了。在某种意义上,喜剧性是我们最好的品质。我不认为我写了非常残忍的趣事;我觉得我写的是相当柔情的幽默,尽管它可能相当生硬和批判性的。不过总的来说,在我写的所有戏剧中,笑声在戏剧结束前就停止了。我无法想像我的任何戏剧在最后十分钟还会真的有任何可笑的事情。不过这不是计划好的,这是直觉。
西摩:昨晚在萨拉·贝克特剧场,观众在看《饯行酒》的时候笑了。你觉得对这出戏剧的这种接受令人满意么?
品特:这得看情况。我非常奇怪他们在尼古拉斯和吉拉的那一场笑了。不过还有其他的笑。当我们认出了人的丑恶,我们自己的丑恶的时候,我们也笑。这很大程度上是对我们自己最恶劣的品性的认识。所以我实际上自相矛盾了。我曾经说笑出自真正的喜爱;而它也出自完全相反的感情,出自对我们的丑恶之处的认识。
阿拉该:根据西蒙·格雷的说法,在《饯行酒》中,你也多少站在尼古拉斯一边。而在很多年前,在谈论《生日宴会》(Bidhday Party)和《归家》(Homecoming)的时候,你说你不会对你笔下的任何人物抱有超过其他人物的喜爱或憎恨。对于你的政治剧,比如《饯行酒》,你会持同样的观点么?
品特:我并不是特别钟爱尼古拉斯;没有他也行。尽管如此,我明白他所处的困境。不要忘记尼古拉斯是一个受骗的人;他是一个着魔的人,事实上在宗教上着魔。他的行动出自一种宗教和政治的着魔。我非常替他感到难过。他完全是一场灾难,不过他所代表讲话的那个社会本身就是一场灾难。回到那个老生常谈——不过这是一个建立在绝对事实之上的老生常谈——他将回家,回到妻子和孩子身边,听音乐,就如萨拉·贝克特剧场的演出所提及的——音乐,完全正确。折磨人的人听音乐,并且对自己的孩子非常和蔼,这在20世纪的整个历史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证实。这是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心理的非常复杂的状态之一。对其中的任何一种我都没有答案,我只是敲打敲打。
我首先要负责的是我手头的作品,而
不觉得对我的大众负有义务或责任
西摩:1962年,全国学生戏剧节在布里斯托举行前夕,你做了一个报告,题目是《为剧场写作》,其中你为艺术的自足性辩护,声称“我所写的东西只对它自己负责。”你依然这样认为么,还是在什么方面做了修正?
品特:本质上说,我想的依然和那时候一样。我觉得我首先要负责的是我手头的作品。我那样说的时候,我真正要说的是我不觉得对我的公众负有任何义务或责任。公众总会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而我对文本负有责任。比如,一群阿根廷人从《旧日时光》(0ld Time)和《背叛》(Betrayal)出发,做了相当出色的表演,这两出戏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政治剧,其中没有政治生活,它们谈的是其他事情。但是对那些戏剧,如同对我的更具有政治色彩的戏剧一样,我都觉得同样负有责任。所以我的首要责任总是指向戏剧本身,无论这是一出什么样的戏剧。我的意思是,我不会改变我的主张;一旦戏剧写完了,我不会做任何改变。
阿拉该:是不是因为这个,你才在这些年中着手执导了不少你自己的戏剧?你是否认为,剧作者是他或她自己戏剧的唯一合法的阐释者?
品特:不。事实上我喜欢看到其他导演对我的戏剧所做的加工。
阿拉该:你觉得导演对他或她执导的作品负有怎样的责任?
品特:在巴塞罗纳,我看了三场我的戏剧的演出,《饯行酒》、《轻痛》(AS代ghtAche),以及《1日日时光》和《背叛》的两场连演。我在所有这些演出中欣赏的是无论导演还是演员都表现出的兴趣。我认为剧场就是包含着兴趣、激情、信奉。它也带来冒险。它不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活动,它是非常危险的活动。不过危险在许多方面都可能出现。比如,我导演的(入土为安》是一出非常安静的戏剧。人们非常安静,几乎不提高嗓音。有许多方式表达生活的这一危险方面,剧场就是表现这一点的。
阿拉该:作为导演,你常被描绘为非常一丝不苟,而你却谈论危险。
品特:这与你问到的我的戏剧写作一样;我希望我既任其自然,又一丝不苟,你可以同时两者兼具。《宴会时间)中有一句谈到死亡,说它同时既快又慢,我觉得执导戏剧也可能同时既快又慢。执导戏剧和参与戏剧的全部问题,是你不知道你在往哪里去,不过你必须找出来,而当你找了出来,你又不知道下一步将会是什么——我相信这里的每个演员都将通过自己的发现知道这一点。不过非常重要的是,不要在舞台上垮掉,说“我不知道我将走向哪里”;你必须站稳,不过这很不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