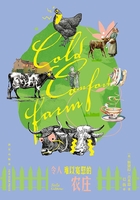十九、匆匆入洞房
此日清晨,荷花和老五老六草草用了早膳,带了银两,置办了几份礼品,便向方家寨走了。
双杏侍奉老母早餐后,便和两个媳妇炒起炒面来,细细炒,文火焙,一锅锅炒面黄澄澄、香喷喷的。那气味窜入老母鼻中,老母疑惑地拄着棍子向厨房走来,她断定双杏在赶制上路的干粮了,叹了口气,欲返回堂屋,可又折回,一声紧似一声地呼唤:“杏儿哎,杏儿——哎。”
双杏闻声走出厨房:
“妈,咋了?叫魂似的。”
老母捣着棍子,说:
“我娃夜里许承的啥?变卦啦?急着要走!我把你个脸朝外的。”
双杏笑脸相迎,回说:
“谁急着要走嘛?”
老母鼻子哼了一声:
“你娘眼麻了,鼻子还没实(不透气)哩!你赶制炒面做啥?还瞒哄你娘咧。”
“妈,迟早要备的。人到齐了,做饭都来不及,哪有锅锅炒面哩?趁现在闲着备好,有啥不妥嘛?焙的金黄金黄的,喷喷香,您尝上一口。”双杏婉言解释。
“不尝,炒就炒吧,反正老娘留不住你,汉子在唤你咧。不过,我可说哩,三五天不许走!”说罢,拄着棍子闷闷不乐地走了。
太阳偏西时分,荷花骑着毛驴,和老五老六带着两个姑娘兴高采烈地归来了。
双杏和梅娘、桂花两个媳妇闻风迎了出去,院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有说有笑,活跃非常。簇拥着进了堂屋,喝茶叙话。双杏和老母打量着新来的两个媳妇,跟荷花介绍的毫厘不差。
荷花喝了茶,边奶孩子边说:
“娃姑妈,你生的儿娃子,一个个能成得很!今日若不是两个外甥保驾,那银子就叫毛贼劫跑了。嘿!把我吓得身子筛糠哩,腿肚子抽筋哩,嘴巴子打牙哩,驴子尥蹶哩;你的两个娃,面不改色、心不慌,把我扶下驴来,各自掏出家什,上了阵。老五的连连子棍,咔嗒咔嗒打得眼花花,前遮后拦,左抡右砸,打得贼人沾不上身;那老六的绳绳甩得飞旋旋,头头上带着个枪尖尖,五花六道光闪闪,也可近,也可远,打得贼人抱头窜。一时三刻,七个贼人伤的伤、残的残、逃的逃、散的散。老婆婆,你看阿姐养的孙孙稀罕(讨人喜欢)不稀罕?!”
老母笑得眯了眼,忘情地说:
“啊呀!荷花,我的好媳妇,我咋头次听你这么会说道,学的一楞一楞的,说的逼真逼真的,叫老娘听故事一样,过了一把瘾。没说的,我娃杏儿本事蛋蛋,生出的娃一个赛过一个,能行的很嘛!噢,都跟了他达──延孝先了么,天下一等一有本事的好男人!要不,你阿姐咋走时站时、忙时睡时,都恋着想汉子哩。”
双杏急了,怕老母说高兴了失口,说出梦中害羞的事来,伸手去捂老母的嘴,说:
“妈,看您夸的没门道了。癞蛤蟆吃豇豆,悬吊着哩。荷花妹子,他舅母,你别多心啊,办成这多好事,你才是本事蛋蛋哩!”
“阿姐说哪里去了,自家人,我多个啥心嘛。”说罢,抱孩子进屋去了。
双杏见四位媳妇俱已到齐,满心欢喜,揣了银子,穿戴起来,带了四个媳妇,由老四老七陪护着,风风光光地去上街。老七陪着母亲,老四和众媳妇紧随其后,群星捧月,簇拥街头。
路人看了稀奇,谁家的大姐领着一群小妹妹逛街?
四个媳妇见婆婆那般穿戴,风姿绰约、光彩照人,个个自渐形秽,无不敬之慕之。
双杏进了布匹店,给四个媳妇每人订做一套便服,一件旗袍。
猛然间,觉得薄了佳纳和花儿,于是,给大媳妇二媳妇也订做了旗袍,算是补结婚时的缺憾。双杏见衣料的花色品种比往日新添了许多,尤其是把衣料搭在媳妇们的肩上比试时,连她自己也看得件件可爱,眼圈热了,心也动了,当年若不是事出无奈,她也做件旗袍跟五哥堂堂正正拜天地多好。这么一联想,她咬了咬牙,决心给自己也补一件。媳妇们是大红大绿大紫,她订了件色泽淡一些的米黄缎。双杏限店主三日做齐。店主嫌急,双杏火了,说:“那就到别的店铺去。”
店主这才满口答应:
“那就三日,咱不睡觉做吧。”
双杏带四位媳妇回到院里时,兄弟贵志和老大已在堂屋陪老母叙话。荷花满心喜悦地正忙着提壶倒茶,倾听贵志带回的消息。
新人旧人一应到齐,大小十七口人,堂屋是人,厨房是人,院里也是人,红火热闹,洋溢着喜庆的气氛。那些远离家门的媳妇,暂时忘却了离情愁绪,和新的家人融合一体。
晚饭时候,贵志牵着骡子死气沉沉地回来了。荷花见了奇怪,迎上前说:
“谁招你惹你来?刚照了个面,天就阴了,咋了吗?”贵志什么也没说,径直来到堂屋,心事重重地坐下,和姐姐陪老母用饭。
双杏何等精明之人,察颜观色,好不疑惑!刚才还笑呵呵的,咋个愁眉不展呢?是因为又猛增几口人喧闹得慌,还是另有他故?直到吃罢饭,也不见兄弟起齿,只得询问:
“兄弟,看你眉目不展,不知有何事作难?说出来有啥不可?兴许为姐的也能担戴一二。”
“没啥作难的,姐。”贵志言语有些吞吐,不比往日利落。
“兄弟,我一家七口,说是探视母亲大人,一月来糟践不少;他舅母跑前跑后,东奔西走,把四个儿媳办成了,人也领齐了,我替你姐夫感谢不尽。只是老母拽住不叫走,若再拖延几日,我这十几口子人可就成灾了。”
贵志不等双杏说完,急急插话:
“阿姐,几十年不遇的一次幸会,兄弟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哩,咋能说是‘糟践’‘成灾’吗?羞煞小弟了!”
“那你说说是为啥嘛?保准是你脸子不展卦,叫你姐看出来了,还不说实话!”老母气呼呼地问。
贵志沉不住气了,缓缓说:
“是这样的,我去给骡子换掌,顶上了赌王。他对我说:“‘小兄弟,听说近来生意不错,明日来,和我陪代理镇长、副会长玩上几把。’我回他说:‘谁不知你是赌王,有钱有势。我一个庄稼汉,做点小本营生,养家糊口,尚凑凑和和,哪有本钱跟你赌?你高抬我了。’那赌王嘿嘿一笑,说:‘你没本钱,兴许是。那一钱半吊的我还看不上;你可叫金子客来赌呀!’我说:‘金子客是谁?我凭啥叫他来赌?’那赌王皮笑肉不笑地说:‘黄贵志,装啥蒜!你当我胡诌冒猜哩。我早就注意到了,近来有金子客出入你家院落,兑换现钱不下四次了,是个漂亮女人,还有跟班的,一打听,原来是你姐姐,对也不对?’逼得我没话说,只说了句:‘她哪是金子客?是回乡省亲的!’就牵上骡子回来了。一路上,我总觉得此事不大好。那赌王、会长、代理镇长沆瀣一气,穿的连裆裤,谁人不知?哪家不晓!为此,有些惆怅。”
老母不听犹可,听了贵志叙说,如五雷轰顶,顿时惊吓得说不上话来。她饱尝赌王诱赌胁赌给她带来的灾难和辛酸。当年的险恶遭遇历历在目,悚目惊心,不堪回首!若不是她丈夫赌光了杏儿的彩礼三两重金,赌掉了家园,她的女儿岂能连嫁妆也来不及置办,连花轿也不曾坐,连洞房花烛夜也不曾享受!这是一个持守贞操的女人毕生最珍贵最珍惜的福分,可都被赌鬼毁灭了,化为泡影。以至害得女儿跟女婿黑夜仓皇出逃!二十多年过去了,本已淡忘的恶梦,在孙孙即将成婚的喜庆时刻,又像魔鬼隐隐扑来,她岂能不惊?岂能不恨!半晌,才恨恨地说:
“这些吸血鬼,咋就改不了害人!”
双杏呢,一时惊得心慌意乱。任凭她当年一个小丫头片子闯过西域,如今又带着五位虎子披荆斩棘,几经绝地而后生,雄姿英发,横闯几千里,老成了许多,但一提及赌棍设圈套,陷阱环生的祸事,她极为敏感,仿佛毒蛇偷袭她的心脏一样,猛猛一惊。赌,曾一度毁了她的家,十几年后,在她老母和弟弟的惨淡经营下,才有了今天。
赌,几乎毁灭了她美好的人生,若不是当年走得快,五哥他人财两空,还得再入军营;她呢,难逃虎口,谁知今日是鬼还是人!她恨透了赌,老早就立了家规:禁赌。赌王逼她去赌,她自然不会去赌。可那帮害人精,他会变着法儿害你,还会连累兄弟和老母。三十六计,走为上!双杏当即决定走!可踌躇再三,不好开口,一是立即要走,怕兄弟多心;二是老母不发话,顾忌老人家伤心。再者,订做的衣物尚未到手,已交了几十两银子订金。为此,虽心事沉沉,却什么也不说。
“贵志呀!就没别的办法可想了?叫人心里七上八下的。”老母愁苦不堪地颤抖着道。
“不行的话,我送点礼,求个情,看咋的?”贵志毫无把握地道。
“那不行。兄弟,要紧使不得!那帮恶棍的胃口,你知道有多大?倾家荡产,也恐怕满足不了他。反倒叫他认为你我软弱好欺,变本加厉。若不是拖儿带女,我就去赌它一次,赢了,立马就走;输了,就灭了他们那伙贼松,方解我心头之恨。可现今我不能。那样做是痛快,结果呢?既害了自个儿,也连累了你们。一个人活在世上好难,难在不能光为自个儿。处世做人,得思前想后,兼顾别人。若只是为了自个儿,那还跟牲口有啥两样?姐想好了,听说书人讲,遇上这档子麻缠事,要用缓兵之计。兄弟,你和和气气、大大方方对他说:姐身子不爽,等候几日。若他逼迫,你就直说:正来月经哩,吊个血裤裆,坐不住,咋赌?”
老母听了兴得一拍巴掌,说:
“嘿!我咋就没想到呢?我娃这招准灵。他不怕冲了财气才怪哩!贵志,就这么着,你去应付。”
贵志也松了口气,佩服地说:
“姐,真有你的,这缓兵之计好,你真能活学活用。”
双杏苦笑了下说:“看你夸的,这是给逼出来的。”
“对!‘兵不厌诈’嘛。好,我的姐姐呀!”贵志兴奋地拍着双杏的肩头道。
老母得意地说:
“你还当是我平日夸你姐,是胡吹冒料哩,今日遇到节疤上,方见她的斧子快哩!”
次日,贵志不经家人知道,请赌王、商会副会长在饭馆吃喝了一场,顺便把双杏的话递给赌王。赌王不得已笑了笑说:“那就过两天吧。”贵志这才舒了口气,老母也心安了许多。惟独双杏不信这个。她暗暗决定,衣服到手之日,便是她回归起程之时。她细细盘算十几口人回归的路费,预计超过东来的三倍:一是人多,二是女人多,大多是第一次出远门,每日不会走多远,住店的时候多,费的时日也肯定多。来时一月有余,六个大人,仅她一个女人,多半路骑着毛驴,五个儿子跟着毛驴跑。生活处处节俭,路程日日趋赶。西归则另当别论了。不管怎样,必须在八月十五之前赶回,要不,她心爱的丈夫会急出病来的;不管怎样,丈夫交给的孝敬钱必须如数奉上。
盘算停当后,双杏从裤带上取出一两黄金,双手捧至老母面前。老母视力虽差,但也觉察了金灿灿的光焰。双杏心里沉甸甸地说:
“妈,您女婿不能亲自来看望您,他叮咛女儿把这份心意带给您,供您养老,您就收了吧。”
老母毕竟视力不佳,疑惑地问:
“啥东西呀?金灿灿的。要让我收下。”当双杏把金子放在她手中用手指一摸时,老母惊了,小声重重地询问:“金子?”
“对,妈,一两。”
老母浑身颤抖起来,说:
“那不行!我老婆子的脸皮还没厚到城墙的份儿上。当年赠的那一两,就够我受用半辈子,咋能收第二次哩!女婿女儿的孝敬之心我领了,金子不能收!”
双杏执意不收回。老母诚心不接受。母女俩僵持在那里。
老母高声喊叫:
“贵志,贵志!跟你媳妇来一下!”
贵志和媳妇荷花闻声来到屋里。老母对小两口叙说一遍。贵志从老母手中取过金子,往双杏手中一塞,难过地说:“姐,你这是干啥嘛!姐夫的心意娘领了,你再这样做,不是剥兄弟脸上的皮么,是算饭钱店钱吗?”
荷花摇着双杏的膀子说:
“姐,你是给我顶工钱?那还有啥人情味儿嘛!好我的姐,你和姐夫的心意我两口子领了,你就别再难为我们,臊架死了!”
老母声泪俱下,说:
“杏儿,快收起来。你我没淘过金,哪知淘金的辛苦!这是你男人提着脑袋,卖命换来的。我听了他淘金的故事,心惊肉跳的。再说,还有十几个娃哩,留着给娃成家吧。我和你兄弟几口人,吃有吃的,花有花的,用不着它。”
“姐,一群人回家,几千里,花费大着哩!”贵志劝解道。
“路费够了。这一份,是你姐夫临走时单另交代的,非收不可!妈,您收了,女儿心就尽了;不收,我给您跪下了!”双杏说着泪湿衣襟,跪了下去。贵志与荷花急忙拦阻。
双杏把金子硬塞给母亲。
老母手捧黄金,长叹一声:
“嗨!我娃孝心太重,女婿孝心太诚,非逼的我——我收了也是心不安啊!”
正在此时,狗叫起来,老母只得收起金子。
贵志出去看门。不会儿,贵志转回,脸色阴沉地说:“代理镇长派人来,叫我去一趟。姐,我去了。”说罢走了。
老母、双杏、荷花听了,心上像压了块大石头,谁也没说什么,可都在思虑,此去肯定带回的是坏消息,谁知那些王八蛋又要耍什么鬼把戏。人人忐忑不安,眼巴巴盼贵志早些回来好弄个明白。
双杏的儿媳妇们七手八脚做好了午饭,由梅娘蓝花端上来,谁也没心吃,谁也不言语,干坐着等贵志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