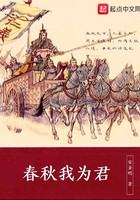清新的空气,晴朗而又微风和煦的午后,宁中直在草地上享受了一个惬意的午睡。暖暖的春风撩拨得人懒懒不愿醒来,半睡半醒之间,宁中直依稀又回到他那张办公桌前,他依旧和邻桌的小王争执于那几十行代码,阳光从窗口照射在地板上,反射的光让宁中直的有些眩目……
耶律倩独自一人骑马沿着湖岸缓缓而行,今天过的很无趣,她并不喜欢狩猎,她喜爱的是汉人的诗词。当她十一岁第一次偷偷跑到父皇的营帐外,偷看前来出使辽国的苏轼,便被苏轼那异于契丹的相貌和豪放而不羁的气质所折服,又听说苏轼是诗词大家,此后苏轼只要在宋朝有新词发表,她便托人将诗词传回燕京赏鉴,俨然一个古代的追星族,然而苏轼的诗词就像一扇门,让她认识了不一样的世界,此后便不可自拔的迷恋汉人的诗词,从此耶律倩的生活不再是骑马射箭,而是与燕京的汉人文人一起研讨诗文。
正当她无趣的四下张望时,一个睡觉的年轻人引起了她的注意。第一眼的感觉也许就是这么玄妙,耶律倩下马悄然走近这个年轻人。一双英挺的眉毛少了几分草原上的粗旷,却多显出几分汉人的书生气和倔强,而让耶律倩嫉妒的那如素丝般白净的面皮配上尖挺的鼻子和微微带着笑意的薄唇,一丝不羁跃然而出。虽然身着是契丹的服饰,但这年轻人的气质却给她熟悉的感觉,对,就是那个她心中最耀眼的明星——苏轼。不知不觉,耶律倩便这样久久望着睡着的年轻人。突然,年轻人的眉头向中间聚拢,眉心耸起一片沟壑,耶律倩不觉伸手想抚平这年轻人眉心的愁结,待到手指几乎碰到年轻人的额头,她方醒悟自己与他素不相识如何能这样亲昵,不由小脸一红。有了一番顾虑心思,耶律倩想起身离开,只是目光一落在这年轻人的眉目间,心中暗自有些挣扎。
宁中直睁开双目,便瞧见一个契丹少女正双眸目不转睛的盯着自己,不由愣住。少女先反应过来,如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慌忙站起身来,向后急退两步。宁中直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自己难道样貌已经有碍市容了?“你这人怎么醒了也不告诉一句,吓坏我了。”少女狠狠瞪了宁中直一眼,一双桃花秋水般的妙眸眼波流转,宁中直不由想起红楼梦中一句名句。“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待宁中直吟完这两句诗便感到要坏事。少女双颊飘起两朵红云,扭身跺了跺脚,便要转身抛开。宁中直急忙拉住少女,手心传来一阵腻滑,少女见挣脱不得,眸中便流转起泪水,下一刻便要溢出。“你这人怎是如此轻薄无赖,快些放手。”耶律倩平日虽与汉人多有交道,但文人们都敬她是公主,礼数周全,言语也小心了得,哪受过今天这等男女接触,嘴上虽是让宁中直放手,但是她现在娇躯无力,心跳得厉害,大半身子倒倚在宁中直怀中。
“唉,嘴怎么就这么快呢,真是罪过、罪过。”宁中直见这位少女虽然嘴里要强,但是动人的娇躯偎依在他身上,似有似无的幽香沁人心智,娇艳欲滴的小嘴。这让就算见过温柔阵仗的宁中直也不禁心跳加快,口干舌燥,哪还能推开这少女。一个酸软无力,一个心有戚戚焉,旁人看来两人倒像一对热恋情人相拥在一起。耶律倩心中惶然,耳边传来的是男人有力的心跳,脑中乱得嗡嗡作响,耶律倩感觉自己好像中了邪一般,想出声呼喊,却兀自失声。
半晌,宁中直忍住心中绮念,为了防止自己动摇了好不容易坚定的决心,宁中直闭目不在望那少女,轻轻扶着少女坐下,又深深呼吸数次,睁眼去看那少女,宁中直傻眼了。只见那少女紧闭双眸,面无血色,手握一把精致的银制小刀,另一只玉手手腕处赫然正在流着鲜血。“我靠,做好人做出人命来了。”宁中直赶紧检查伤口,幸好少女力道弱没有割正位置,(实际是耶律倩力气尚未恢复,又晕血,这才没成功)宁中直慌忙从身上撕下一块布条,刚待给少女包扎,突然感觉布条不够干净,怕引起感染,眼见少女的袍子素白似雪,于是便从少女袍上撕下一块布条。也许是这声音挑动了少女敏感的神经,少女倏然睁开了双眼,只见那人正在撕自己的长袍,少女羞愤异常,“你……”。宁中直闻声抬头,只见少女刚想说话,头一歪,又晕过去了。宁中直真是狂汗,“完了,完了,自己是做实了淫贼的名号。”宁中直一边哀叹自己英名不保,一边手里没停,迅速简单包扎好少女的手腕,然后把少女扛在肩头,向坐骑奔去。
等宁中直怀中抱着少女驰回营地,从进营门一刻开始,一种古怪的气氛便洋溢在所有和他照面的人们之间。宁中直预感自己多半又是做了什么超越世人常识的标新立异之事,“不就是公然抱了个美女嘛,哼,就把你们羡慕成这样。”宁中直的心理调节能力一向超越常人,这次也不例外。宁中直也搞不清营中何处有郎中,于是便骑马赶回自己营帐,准备找萧革撒利去寻郎中。萧革撒利正在自己帐中裹着毛毯烤着炭火。今天的事真是让他哭笑不得,这位宁先生怎么就不让他清净呢,正在感叹,亲兵进帐禀告宁中直归来,萧革撒利赶忙扔下毛毯,掀帐而出,只见宁中直正驾马向他而来,怀里抱着一个少女,只是面目看不清楚。宁中直正要去寻萧革撒利,见他在前面等候,倒为上午的事有些羞赧,下了马便和气的对萧革撒利说:“萧革撒利,快寻个郎中来,这少女割伤了手腕……咦……你怎么跪下了,嗯?大家都跪下了,这……这是咋了?”宁中直还迷糊着,萧革撒利哪有时间回他的话,已经赶紧一面派人去寻御医,一面通知辽道宗。分派妥当,萧革撒利才小心翼翼的轻声告诉宁中直:“宁公子,这位是当今圣上的女儿,陈国公主耶律倩。”宁中直就算神经再大条,也被这消息砸的七晕八素。宁中直从来没感觉自己脑子这样乱过,恐惧,惊慌,怀疑,甚至有一丝自豪都在脑中辗转轮回。
萧革撒利见宁中直听见他的话后和自己预想的差不多,心中略感宽慰,心想这位特立独行的宁公子总算还与常人有相同的地方。过了一会,萧革撒利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哈哈,泡了辽国的公主,我还真是人才呀,哼哼,太有才咧。”宁中直洋洋自得的自言自语起来。萧革撒利听了他的话几乎晕倒在地,这宁公子还真不是人啊!宁中直抛下成为石像的萧革撒利,扬长而去。
其实宁中直已经想透其中关节,公主醒来之前,没人会知道事情缘由,而依自己观察这位公主的性子,醒来之后发觉自己没有破坏她的名节,多半也不会声张,而是寻个由头便抹平此事。回到帐篷,宁中直还没有从那种有如中了大奖的情绪中恢复过来,毕竟在后世,宁中直没少看这个国的王妃,那个国公主在大众面前的光鲜知名度,宁中直心中洋溢着巨大的虚荣心带来的满足感。
晚上,宁中直刚吃完一顿丰盛的晚餐,一位辽道宗的近侍便来到宁中直的毡帐,辽道宗宣他去晋见。宁中直见来人神情恭敬,也不是兵将来请,心中便已经大定,知道自己猜得八九不离十,于是便从容不迫的跟随来人向大帐前行,萧革撒利在旁看后佩服得五体投地,果然不是人,呃,不是一般人。
实际上耶律倩在回来路上便被颠簸弄醒,只是女儿家面皮薄。中途她悄悄睁开眼睛,自己正靠在那年轻人温暖的胸膛上,年轻人正全神贯注看着前方。耶律倩见他并未对自己无礼,而手腕的伤口也被他用拙劣的手法包扎上了,心中便也不是那么对他抗拒。听着他的心跳,鼻中也充满了他身上一种温婉平和的气息,加之之前受惊,实在有些倦怠,渐渐在宁中直的怀中进了梦乡。
辽道宗和陈国公主耶律倩正在大帐中等待宁中直的到来,耶律倩枯等之时,不由忆起下午和他在一起的情景,一丝灿烂的微笑自嘴角飘出。正当此时,帐外一声让她又怨又喜的声音传来,“宁中直求见大辽国皇帝陛下。”耶律倩慌忙注视起大帐帷幕处。那个恼人的家伙走进来了,却口观鼻,鼻观心,一眼都不看我们美丽可爱的陈国公主耶律倩。“宁先生,谢谢你从凶徒手中救下小女,朕宣你前来是感谢你对小女的救命之恩。”辽道宗温言道。宁中直心中此时别说有多别扭了,这“凶徒”可不正站在辽道宗面前么,可还是义正言辞的沉声说道,“在下碰巧遇见公主遭人侵害,岂能袖手旁观,这是义不容辞,陛下言重了。”说完还是很不自然的瞄了一眼旁边的少女。少女一双妙眸正盯着他,见他进帐后第一次看自己,不由心中恼他,狠狠瞪了他一眼,只是效果缺缺。和上次一样,宁中直感觉自己又被狠狠“电”了一次,而且电力比上次更足,差点把宁中直的双腿电软。宁中直不再敢看旁边的少女,客气推辞了一番辽道宗的谢意,便落荒而逃。
宁中直回来路上,还在回味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眼,这位陈国公主耶律倩真是媚态天成,即便发怒也是似喜似嗔,惹人恋爱。宁中直回到自己的帐篷,一掀开帷帐,帐内并未点灯,但借着从帐缝泻入的月光让宁中直发现帐内还有一人,宁中直心中一紧,便要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