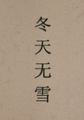1
我陷入了困惑之中。
我还要写字么?我不写字去做什么?去打麻将、扑克?我不是没有上过桌,我也打麻将、扑克。我是一个随和的人,我要朋友,不会拒绝朋友的请求,在他们三缺一时,我会应邀上桌凑对,只是,打麻将,我偏偏记不住怎样算和、怎样找宝,更不知道帮哪家、吃哪家,我就是一个另类,在麻将桌上,我没有朋友,没有敌人,我只是一棵孤零零的树,任狂风吹打;是一只折断翅膀的鸟,把自己****的身体暴露在其他人的枪口下。打扑克,我不会组合,不会周旋,只会硬拼,使得朋友们哭笑不得。几次以后,他们说,你的心不在这里,不要勉强自己,你去看书、去写字吧。朋友们下了判断,我不读书不写字不行,那我还能怎样?读书,给了我一个新鲜的世界,教我认识一批人许多事,我不寂寞。写字,是我生活着、思考着的表现,是我生活的另一种形态。萨特说,我思故我在。我说,我读着、写着,故我存在。
我该写怎样的文字?自幼时,我一直醉心的是文学作品,读得多了,就写,尤其是参加中文函授学习在教师精心指导后,我也发表了一些散文、小说,好像并没有遭受其他人遭到的挫折,说是写了数十万字一个字也发表不了,或许是缪斯女神的眷顾吧。只是,发表了又能怎样?有几个人认真看了,有几个人懂得我的表达法呢?反之,要么去写新闻、社会纪实?想想自己写的不多的几篇,闹得鸡飞狗跳的,影响力蛮大,只是,我要这影响力做什么?抬高自己身价,搭建进步平台?这样想太卑鄙,把文字作为敲门砖不是我想要的。但是我想到匡副总编说的,宣传是工具,既然是工具,那就要看看工具掌握在谁的手里,我现在掌握了工具,那我可以凭着自己的判断写自己想写的文字。
谁也不能勉强我。
2
中央出台了退耕还林政策。
大哥找到我,问,村里干部宣传退耕还林,说开发一亩荒山栽多少棵树,上面会补稻谷、补钱,一补8年,你说这事做得不。我说,这是好事,既绿化荒山,又能进钱、进粮,你考虑自己能力,弄个几亩。大哥高兴走了。
经过许多年的过度开发,太平镇的山已经见不到多少有用材了,民谣说,远看是青山,近看无用材,丘陵、山坡上覆盖的全是茅草,春天郁郁葱葱,很繁茂的样子;一到冬季就露出了真面目,茅草枯了,苍黄一片。如果想到山上找几棵树,要么是小得像人的手腕,要么是歪脖子,绿化荒山成了必须。现在,中央出台退耕还林政策,是一个民心工程,是大好事,我决定以这个点去找找素材,写一篇新闻稿。
跑了一些村,问起退耕还林的事,多数人不清楚,也没有可以看的,谁知,我偶然到镇政府大院玩,却看到了生动的一幕:天上下着牛毛细雨,一辆满载树苗的卡车缓缓驶进镇政府大院,车还没有停稳,3个中年汉子就爬上车厢,使劲把树苗往车下扔,嘴里还算着,一捆,二捆.。。不一会,车厢里的树苗被扔成3堆,三个汉子跳下车厢,衣服、嘴脸上全沾着斑斑点点的泥巴。一个瘦小些的汉子笑着骂一个肥胖的大汉,说,你抢起树苗,比抢老婆还来劲,你们村到底准备退耕还林多少亩?肥胖汉子咧着嘴笑,说,我们村计划退耕还林1000亩,准备争个全镇第一,我不抢还行?听到这里,我明白是怎么回事,马上走过去,问起3个汉子的情况,原来是3个村的支书、主任,今天得到有树苗的信息,早早等在镇政府,抢了树苗好回去退耕还林。
这不是现成的新闻么?我离开镇政府,以《抢树苗》为标题,写了篇现场新闻,马上送邮电所寄《清江报社》。
第二天下午,我接到《清江报》社匡总电话,他非常兴奋地说,退耕还林在我县才刚刚部署,你就送来了鲜活的新闻,这将有力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好好,我已经安排在《清江报》一版重要位置刊发。接着,他自言自语说,古老师,你既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又有较强的政治洞察力和新闻敏感力,你就没有想过到报社工作么?我的心热了一下,马上说,我会努力的,谢谢匡总的关怀。
几天后,镇政府办公室秘书到学校找我,说朱书记请我到镇政府去,有事商量。我向几个老师交代一番,请他们帮着照看学生,骑着自行车跟在秘书的摩托后面,向镇政府疾驰而去。
朱书记在办公室等我。我刚在门前打声招呼,朱书记就离了座位,兴冲冲奔向我,一把抓住我的手摇着,你可帮了我大忙,我今天专门请你吃饭谢你。说完,交代站在门口等招呼的秘书说,你去安排一桌饭,标准要高,记得通知镇长、人大主席、副书记,还有在家的班子领导,就说我们请古老师吃饭。
我不清楚朱书记要摆个这么大架势干什么?就为我写了几篇新闻?我梳理一下,那篇写贫困学生的,算是中性报道,没有给他添彩;那篇财税提前过半的,算是给他火了一把,传言说他要调城里,谁知没有如愿;接着,我弄出个太平中学学生出走的稿子,不知影响他没有;这次,写了村干部抢树苗,看《清江报》匡总来电是非常满意,但是朱书记怎样评价,我还不得而知。
朱书记把《清江报》铺在办公桌上,指着头版报眼位置的《抢树苗》新闻特写说,写得好,写得好,你知道么,分管这项工作的是县委副书记,他一看完就打电话给我,称赞我镇工作有前瞻性,做得扎实。他还提到太平镇财税提前过半的事,说太平镇工作平衡发展,进步快,太平镇的干部应该放到更好的岗位。朱书记一口气说完这些,又抓住我的手,摇着,说,古老师,你是我的福星,你帮了我大忙,你知道么,下半年县委就要考察班子了,你知道我年纪偏大,只晓得做事,如果下半年还不能进哪个局,我只能在乡镇退休了。谢谢你,谢谢你。
朱书记的手有劲,温暖,传递着对我的真诚,我由衷高兴,谦虚说,这些事是你为首的镇班子安排得好,我只不过是如实反映了,要谢,还是谢你们自己。朱书记哈哈笑着,回到椅子上坐下,说,你也听清了我已经安排镇班子来陪你吃饭,我知道你酒量一般,你不用怕,他们敬你的,你喝不了,我代,谁叫我是你老哥。听到朱书记与我称兄道弟,我很高兴,我不喜欢与戴着官帽的人打交道,但是,我喜欢把官帽藏着掖着的人交往,在我感觉中,朱书记与我大哥差不多,就是我兄弟。
朱书记怎么不问镇中学学生出走的事呢?那可是一篇3000多字的稿件,很吸引眼球的。我想,要不要主动谈谈有关的事。正犹豫间,朱书记捏着一支钢笔敲着报纸说,中学女生出走的稿件我也看了,这是严肃的教训,严肃的教训,我把朱校长叫到办公室来狠狠批评了一顿,学校不能只教书不育人,我告诉他,你能管好学校就继续当校长,不能管好学校就走路,太平人才多的是,比如那个古钟老师,文章写得好,名气大,怎么一直安排在村小呢,明显不合理。这个观点,我还与教育局长交流了,他答应下学期一定调整你的岗位。朱书记盯着我,我露出一丝笑容,连声说,谢谢书记关心。
朱书记缓和了脸色,用探寻的目光打量我,征求我的意见,古老师,你以后写好稿件,能不能送我看看,我一方面学习学习,另一方面给你提供材料。我懂得,他要审查我的稿件了,这不是太不尊重我么,稿件审查的责任在报社,你一个乡镇领导怎么能干扰我新闻写作呢?我心里不痛快,但不想表现出来,于是,我搔着头说,行,行,以后写了稿都送书记看,只是怕你忙。
朱书记站了起来,摇着手说,不忙,不忙,你古老师的稿件,我再忙也会学习的。
秘书在门口说,书记,饭做好了,其他领导都在等着。
随着书记去食堂时,我想,这顿饭我一点酒也不能喝,就说我胃痛。
文字是我的工具,我可不想成为政治的工具。
3
时值盛夏,正是“双抢”时节,也就是既要抢收、又要抢种,这可是我最辛苦的时节。
我违背了少年时候的诺言。记得初中会考后,有一次进大山砍柴回家,因为太累,我把戗棍扔了,说是再也不砍柴了。爹娘没有发火,反而称赞我有志气,说我一定有出息。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妻子依然吃农业粮,按照孩子随母亲户口的原则,我的孩子也还是农业户口。
事情好像绕了一圈,再回到出发地,爹娘在我跳出农门后绽放的希望如被点燃的烟花一样飘散得无影无踪。
我一共接触过两个女孩。当然,我的同学刘杏花不在其中。
一个是我家附近村子的女孩,家里开杂货店,自己在镇皮箱厂上班,天天骑着一辆桔红色的女式自行车经过我家门口,夏天,她戴白色遮阳帽、身穿白色长裙,像一朵云飘过;冬天,她戴绒帽、穿鲜艳的毛衣,像一团火一样飘过,这是一个独立于乡村的女孩,被我注意后,她迅速吸引了我。我被少年维特式的激情折磨,也非常看重自己国家干部的身份,所以,有一天,我等在乡路上,看她慢慢近了,礼貌地招呼她停一下。她狐疑地看着我,一只脚踏在单车脚蹬上,一只脚偏在地上。我强作镇静地说,我写了封信给你,请回家看看好么?说完,从口袋中掏出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信。她的脸迅速红了,右手捏着信,也没塞口袋,脚一蹬,很快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
信的优势是可以叙事,可以抒情,容量足够大,我相信我的信已经完全表达了我对她的爱慕,一定能够征服她的芳心。果然,第二天,看见等在路边的我,她放慢了车速,红着脸,用征询的眼光看着我。我说,我陪你回家。之后,骑着自己的单车跟在她后面,轻松自如地聊着天。
过了一段时间,她告诉我,新婚姐姐要回门,有几桌客人,她爸妈邀请我去吃饭,问我能不能去?我想,这顿饭不能吃,我与她才相识不久,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现在她家的客人来了,我往她家一搅和,他们一定会认为我们是一对,这个结果,对她不好,对我也不好,我们还需要时间熟悉,需要培养感情。于是,我对她说,对不起,我很忙,去不了。她一听,脸色煞白,咬着嘴唇,骑着车就走了。
以后,她再也不理我了。不多久,她就与一个镇干部的儿子订了婚。
对这个结果,我不怪她,甚至不怪自己,我想,爱情是应该经得起时间敲打的。
另一个女孩的爸爸是区委副书记,自己在电站上班,我相信她的工作一定是她爸爸利用职权安排的,想到这些,我心里有点怪怪的。偏偏她自视极高,第一次见面就问我工资多少,感叹小学教师没地位,她笑着问我,如果学生把屎拉在裤子里,你真的会去帮他洗干净?我点点头,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怎么能不洗呢?我想,如果不是一个亲戚做的介绍,我真的要好好奚落她一顿。
我知道,我与她不是一路人,勉强见了几次面,我们就没有往来了。
我现在的妻子,在认识我以前,自己学的缝纫手艺,租了店面卖布、带徒弟。我们交往一段时间后,按照乡村婚俗看大姑、订亲、结婚,一项都没拉下,只是,我妻子为了婚礼,把自己的积蓄贴进去不少。
当然,她也提了条件,结婚后一个星期,我们到镇上租店面做老本行。
几年来,妻子主要时间做生意,我教书,附加种家里的2亩责任田,大家都不轻松。
我满足于这样的生活状态。爹说过,不论哪个朝代都要教书先生,这只是功利的、实用的说法,在教学中,我体会到教书的乐趣,比如,我离开福原已经好几年了,但是还有一些学生专门来看我,比如那个绰号山猪的池水平,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前年,专门寻到镇上找我,说是猎了只野猪,送些肉给我吃。我非常高兴,自己下厨房做饭,边喝酒边聊天,问了许多学生的近况。
我边教书,边学习,边劳动,边写作。中文函授大学毕业后,我接着进修鲁迅文学院函授,参加法律专业自学考试,我们做教师的有一句口头禅,给别人一瓢水,自己就必须有一桶水,这是工作的需要,也是完善自我的需要,无论学习什么学科,我总能品味到其中的乐趣并乐此不疲。我热爱劳动,我相信我是一个脚掌必须踩在土里的人,这样我才心安,我才能写出我想写的文字。
太阳的光把我背上的肉晒熟了,我似乎闻到了烤肉的焦味。
其时,我正专心致志地对付一块水田的水稻。
金黄饱满的稻粒坠得稻杆深深垂着腰,就好像我深深弯着的腰一样。
面对土地,面对丰收,我必须虔诚。
水稻一排排被我安放在后面,他们经过几个月的生育以及筋疲力尽,该休息了;掩藏在稻草中的虫子,身体碧绿纤长的螳螂、身体肥胖灰白色的飞蛾、黑褐色的小屁虫,在我的前方与我的镰刀赛跑,脚下的水因为有稻子的庇护免遭太阳的荼毒感觉是清凉的,好像是我的另一种方式的呼吸。
这个热腾腾的夏天,这个生机勃勃的季节。
我想,如果离开这些田地,没有了稻子的陪伴,拒绝田野生物的爱抚,我还有什么?这就好像我写的文字,不写我身边的人,不触摸他们的心跳,不去品味他们泪珠或汗水的滋味,这些文字有存在的必要么?
我的文字只能是镰刀,要么我掌握,要么是交给需要镰刀的人掌握,它永远不可能是一副装饰画,去装饰某些人的厅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