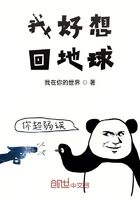挖心?如此恐怖的字眼,我只是在恐怖电视电影里看到过,没有想到居然会发生在这民风淳朴的小镇子上。
亮子说完,就加快了脚步,我寻思着,难怪了,我今天在街上没有看到什么人影,敢情这镇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
说着话,我们就到了自动取款机的前面,亮子毫不犹豫的就给我取了一万块钱,递给了我,说是不够,他可以回家帮我弄点儿。
“够,够,真的谢谢你了亮子,我?”我看着亮子,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亮子摆了摆手:“你跟我谁跟谁?你这么说,那就是打我的脸。”
他说罢,便拍了拍我的肩膀:“你怎么这么冷的天就穿这么点啊?”他这才开始仔细的打量起我来。
又拽了拽我的裤子:“大过年的,还穿个破裤子啊?”
这条裤子的膝盖边缘都已经在山里给磨破了,我尴尬的笑着说,这不是流行么,亮子摇头,直说这样的流行他欣赏不来。
我们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一路聊到了局子门口,突然亮子猛的回过头去,朝着身后仔细的看了看,然后就皱起了眉头。
“怎么了?”我问道。
“没有,好像刚刚有人在跟着我们。”亮子的目光在远处的拐角停留了一下,然后狐疑的摇晃了一下脑袋,说道:“可能是我最近因为“挖心”的案子精神太过于敏感了。”
他说完,就转身走进了局子里,我跟在他的身后,也忍不住回头看了几次,就连一个鬼影子都没有,应该是亮子想多了。
“你们回来啦。”金巴回过头看着我们。
兰香姐依旧又陷入了昏睡之中,她现在清醒的时间依旧开始变得越来越少了。
“嗯,走,我先送你们去我的宿舍。”亮子说着又从桌上拿了钥匙,便带着我们一起到了警局后面的宿舍了。
这宿舍一共三层,还真的别说,比我们殡仪馆的宿舍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儿的,一间也正好上下铺一共四个床位,我们刚好住。
“柜子里有好几床被子,你们今晚先休息,我还要回去值班。”亮子说着就给我们关上了门。
金巴将兰香姐抱到了床上,盖好了被子,便打着哈欠,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
我原本也想早些上床休息,不过冯叔却是凝着眉表情异常的严肃,他快步走到宿舍的窗户前面,然后不顾外头还有大风就推开了窗。
“呼呼呼。”
寒风立刻从窗户外头就灌了进来,冷的我直哆嗦。
“冯叔,怎么了?”看着冯叔的举动如此的怪异,我便知道一定是他觉察到了什么。
可冯叔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有快速的将窗户给关了,并且迅速的从自己随声带着的布包里抽出了三张黄符。
沾上了朱砂就写了一些我完全看不懂的符号文字之类的,然后就把符贴在了门口和窗户上。
而且,这一贴就是八张。
“冯叔,是不是哪儿不对劲儿,这里有脏东西吗?”我紧张的问冯叔。
冯叔冲着我摆了摆手:“没事儿的,早点儿睡,记住,夜里无论听到多么大的动静,都当作没有听到,不要理会就是了。”
“啊?”我听冯叔这么说,心中就更是没有底了。
敢情还真的有脏东西啊?我蹙眉分别看了一眼门和窗户心情很是复杂,金巴却已经打起了呼噜。
冯叔爬到了上铺,便侧身睡了,我也尽量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立刻爬上了床,结果一躺下,便看到了一颗脑袋,吓的我瞪大了眼眸,再仔细一看,是赵老师。
她正在屋子里飘来飘去,我微微咳嗽了一下,她便朝着我飘了过来。
“赵,赵,赵老师啊,您也休息吧。”我还是不适应她这么披头散发穿着红裙褂,在我的面前飘来飘去的。
这比恐怖片,还要让人心头一紧。
“我没有地方可以躲。”赵老师的与其很是平淡,我想是不是做了鬼之后就没有了喜怒哀乐了?
不过,冯玲有时候还是挺活泼的,都是横死,区别也太大了。
“对了,明天让冯叔给你弄个稻草人,好让你住。”我都把这个给忘记了。
赵老师点了点头,便默默的立在了柜子边上,我这个斜角正好可以看到镜子,镜子里没有东西,而镜子前却立着一个人,看起来还真的是挺诡异的。
我闭上眼,不打算再分心,准备好好睡一觉,明天买最早的火车票离开这里。
“咔咔咔,咔咔咔。”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就听到门外有咔咔咔的好像是拧门把的声音。
这让我瞬间就从迷迷糊糊中变得清醒了过来,想着是不是亮子回来了?
“咔咔咔。”
门外的动静越来越大,我不禁开口问道:“亮子?是你吗?”
门外没有任何的回应,但是仅仅安静了几秒钟之后,就响起了敲门声。
“叩叩叩,叩叩叩。”
这一次就连打着呼噜的金巴和都给弄醒了,冯叔却还背对着我,侧身睡觉,我想可能是上了年纪,睡着之后就会比较沉才没有被吵醒的。
“谁啊?”金巴也嚷嚷了一声。
“砰砰砰!”
门外从敲门声变成了粗暴的拍门了,金巴从床上爬了起来,就穿上鞋准备出去了。
我立马叫住了金巴:“别去,我觉得不对劲。”
“哪儿不对劲儿了,这不是村子里,没有那么多的神神鬼鬼的东西。”金巴说完就准备去开门。
我迅速的从架子上下去,而金巴的手恰好放在了门把上,而这个时候,门外那暴躁的拍门声也戛然而止。
“别开。”我说着便一把抓住了金巴的胳膊。
金巴的身体一僵,手中的门把却发出了咔嚓的一声,我条件反射的就一把按住了门。
“怎么了?”金巴见我反应如此大,也吓了一跳。
“你没有看到这四张符吗?是冯叔贴上去的,我想这里,不干净。”我此话一出,金巴的脸色立刻大变。
然后迅速的转身就朝着兰香姐走去,一屁股坐在了兰香姐的身边,一脸紧张的望着兰香姐。
“这什么情况?要么就完全遇不着,一遇上,就没完没了的了?”金巴念叨着。
我蹙眉,看着门上的这四张黄符,突然觉得这几张符我好像有那么点眼熟?不过这种东西应该都长的差不多吧,估摸着就是在殡仪馆的时候见过不少。
“你休息,今晚,我就在这门口守着。”我说着就拉了一把椅子,直接就坐下了。
明知有东西找上门了,想睡只怕也睡不着了。
金巴叹了一口气:“我心得有多大啊,还睡觉呢?我可睡不着了,我看着兰香你睡吧。”
他的黑眼圈重的很,不过因为他的态度很是执拗,我也就不劝说他了。
金巴自己可能还没有觉察到,现在只要一碰到危险,他就会特别的紧张,不是因为贪生怕死,而是特别在乎身边的那个女人。
我和金巴两人就这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坐就是一晚上,第二天窗外蒙蒙亮,我便腰酸背痛的站了起来。
准备出去洗漱洗漱,然后就去跟亮子告别。
正准备起身,门外就响起了敲门声,金巴紧张的跟我对视了一眼。
“谁?”我警惕性的问。
“是我,亮子,起来了吗?我给你们送早餐来了。”门外传来亮子那熟悉的声音,我这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立刻打开门,把亮子给请了进来。
昨晚估摸着是天太暗,亮子没有注意到,我和金巴都是一身的泥泞,金巴进来把吃的一放,就开始给我们找衣服。
都是厚厚的棉衣,抗冷的。
“谢谢亮子,我这?”我的心里是暖活活的。
“谢什么谢啊,看看你们这一身,快洗洗去换上,大过年的也不嫌寒碜,洗澡间就在外面,让金巴带着你去。”亮子说着还扬了扬袋子里的毛巾牙刷。
他这做经常的,心是够细的。
我和金巴轮流洗好了澡,进来的时候看到冯叔依旧在吃饭了,兰香姐醒了,不过面色比前几天都惨白了。
亮子一个劲儿的让兰香吃点东西,可是兰香姐的目光却一直盯着亮子的脖子,那眼神就好像是会发光一般。
“那个亮子啊,兰香怀孕了,胃口一直不好,能不能麻烦你下去给兰香姐弄一份血豆腐?”我一是要把亮子支开,二是兰香姐确实是要吃点血腥味儿的东西了。
“啊?血豆腐?那太腥了,兰香姐这么重口味啊?”亮子皱着眉头看着兰香姐有种难以置信。
“那个,不是怀孕了吗,孕妇都这样,口味重的很,对了,那血豆腐别煮的太熟了啊。”我提醒亮子。
亮子点了点头,依旧是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兰香姐,不过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问,乖乖的去给我们买血豆腐了。
我迅速的将门关上,看着兰香:“兰香姐,你怎么了?”
“小天啊,我快疯了,我满脑子都是血,我好渴,我好饿啊。”兰香姐痛苦的掐着自己的脖子。
“兰香你别这样,别这样,我们给你想想办法。”金巴说着就紧紧抓住了兰香姐的手。
结果兰香姐就好像是发了疯一般将金巴的手用力的甩开了,嘴里还喊着:“别靠近我,别靠近我。”
兰香姐将金巴推开,而她的眼睛里却是泛出了恐怖的红光,这种红光之前是她吃饱了之后才会出现的。
可是现在,她的眼睛就已经红的跟兔子的眼睛差不多了。
她自己也觉察到了,扭过脸去不看我们。
“咕噜噜,咕噜噜。”
她不看我们,但是,她的肚子却依旧是咕噜噜的叫唤个不停,这让兰香姐很是痛苦。
“兰香姐,你等等,一会儿亮子就送血豆腐上来了。”我安抚兰香姐道。
兰香没有吭声,但是肩膀却是抖动个不停。
“冯大叔,兰香没事儿吧,她,她现在这样还正常吗?”金巴是忧心忡忡。
冯叔看了一眼兰香,将最后一口包子塞入看自己的嘴里,说道:“这只不过才刚刚开始,痛苦的还在后面呢。”
“什么?”金巴的瞳孔瞬间就放大了好几倍。
“阴胎其实应该过了十天之后才会是闹腾的最厉害的时候,她这个孩子看来比其他的阴胎还要厉害,现在她想要喝血,就跟着了道一样,是完全控制不了的那一种。”冯叔说完,就看了看我和金巴:“别靠的太近,小心被咬破了脖子。”
“呃,有这么悬吗?”金巴蹙眉,觉得冯叔有些夸大其词了。
可是冯叔是不会拿这种事儿来开玩笑的,房间里一下子就陷入了沉默,这才仅仅只是第五天啊。
“呃呃呃。”
兰香的喉咙里发出了低低的叫声,我们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就朝着房门口冲了过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恰好门咔嚓的一声打开了。
亮子的手上还拎着血豆腐,兰香姐一句话都没有顾得上跟亮子说一把夺过了血豆腐就直接用手抓着往嘴里送。
吃相极为的狰狞,看的亮子目瞪口呆。
“呵呵呵,兰香姐真的是饿坏了,那个亮子,让他们先吃着,你陪着我一起去买票怎么样?”我是一秒都不敢让亮子在这里呆。
就怕亮子看出了这其中的猫腻,把金巴扯进来我就已经够不是滋味了,我真的不想再把亮子给扯进来。
只是,亮子听我说买票,便摇头:“买不来了。”
“什么买不了?”我狐疑的看着他。
“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镇上发生了多起恶性事件,现在火车什么都已经停靠了,还有出镇的路口也全部都封死了,为的是抓住凶手。”亮子说道那个挖心的凶手,脸上就露出了无比严肃的表情。
而我们几个却都听的傻眼了,居然不能离开?那我们怎么找人去救苗苗啊?
“不是亮子,我有很急的事情,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我恳求着亮子。
亮子很是为难,我知道,他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民警没有那么大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