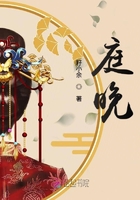我:事实上爱情的本质和钱没关系,我们把爱情的步骤拆解一下,牵手,亲吻,诉说,做爱,这些不需要成本。但钱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在海洋公园牵手,我们在阿尔卑斯之巅亲吻,我们在星巴克诉说,我们在海景房做爱。言语依然是我和你,动词没有变,但是定语状语变了,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到了二十二,二十三世纪,它们还会再变,可做的事没变,爱与美没变。妈呀,我怎么成了一个古典主义者了?肯定是我现在很穷的缘故。
出:那你会有经济压力吗?
我:我自己一个人不会有,一天两顿饭三包烟,一本书可以让我愉悦好几天。但是一旦走出家门这种压力就会存在。我不觉得钱重要,可社会大环境的标准是,穷意味着无能。当然我一直在与清贫致远的人做朋友,但这种事会不请自来。比如有一次,我和姚远和张珏在东直门的咖啡馆打牌,身后有个跟我们差不多大的男孩跟朋友打电话,说接了一个小活,需要点本钱,现在手头有四千,问他借三千,剩下三千他再去搞,这样,一个亿就有了。就那一刻我们都没心思再玩十块钱的斗地主了。我们仨写了那么多本书,花了那么多心血,做了那么多年的自我修养。这时候来一陌生人,他张嘴报的钱比我们三个写的字还多。你让我们怎么办?让我们怎么还能骗自己说,文字是至高无上的?
出:你再讲一些,感觉很对。
我:好吧,我说说sasa,她做时装秀,每个秀都会有主题。有一次她想把四大时装周和她那场秀连在一起,纽约,伦敦,巴黎,米兰,最后结论是,穿在杭州。她问我怎么办,我建议她采用达利那幅《记忆》,制作些柔软的表,绘上四个城市的时区贴现场各个地方。她觉得不错,我们就去买材料,每块软胶嵌十二个扣子。因为买的少,卖扣子的女人不理我们,她在电脑前炒股,让我们随便挑,把钱扔盒里就成。我是陪sasa做事,冷漠的服务态度已经让我很不爽了。下楼的时候sasa讲,别看这些人土,他们的财产都起码几个亿,像那个卖拉链的,她在义乌的库房有一亿个拉链,在杭州放一亿个,光是拉链就价值两个亿。你爸妈也是这样吗?我问。事实上,她说,比这些人做得大。她可能意识到她伤了我,忙改口说钱只是个数字,你赚到第一笔钱就考虑投进去赚第二笔钱,根本舍不得也没时间花,她不想过那种被钱套住的生活。我知道她在安慰我,我难过地就是感觉到她为什么安慰我,因为她看到了我很羞耻。你能明白我意思吗?我羞耻而惭愧。
出:我明白,没钱本身不羞耻,但社会强行附加给你羞耻感。
我:真棒,欢迎回到地球。
出:你这次很真诚。
我:我一直很真诚,只是这次我没有用我的幽默去掩饰。那天回来她开车,她坐前排,我坐后排,我俩从来没这么坐过。她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快到她公司时我问她——整个批发市场,那么多个有钱人,其中有一个人听说过达利吗?
出:所谓财富要重新定义,需要一个双重标准。
我:对,那会降低失败艺术家的自杀率发病率。
出:再说点别的吧,还有别的意见吗?
我:还有一个,对未成年少女怀孕怎么看?
出:这个不好,你别写,不健康。
我:了解。
出:你说我儿子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呀?
点点打电话来说过意不去,前几天不在深圳,害得我白等好几天。我问她今天晚上干吗。她说得给一个朋友过生日,跨零点的那种,在BBF的V3。
“你不是说周日才回来?”我问,“今天才周三。”
“朋友过生日嘛,这么大的事当然得赶回来。”她说,“你也别难过,你下次来深圳我请你吃饭吧。”
“我现在就在深圳。”
“你等一下,”她捂着话筒仿佛在和身边人讲话,“我经纪人告诉我她又接了三场演出,估计要再下一个周日才能回深圳。”
“你今天晚上要在BBF的V3给你朋友过生日Party。”
“要死啦!我应该先问清楚你的,再讲我的。”
“你一直在深圳,根本没去新加坡。”
“但我以前去过新加坡嘛。”
我去得早一些,我想在她的朋友High起来之前先跟她聊会儿。点点问我,她看起来怎么样。我说很好看,比过去更好看。
“你也是,”她回应道,后又审视我一番,“其实不是,但也还好啦。”
“我没问你我跟过去比怎么样。”
她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说:“你就一直在深圳等我?”
“不只是等你,每天还会看六个小时电视和睡八个小时觉。”
“你早说呀,我就带你出来玩了。”
“我早说了。”
她瞪眼睛,仿佛我不可理喻。两个男孩过来打招呼,她跟他介绍我是个作家,从北京过来的,采访过她。她坐下来看到我表情不对,说:“讲多了他们会八卦,很无聊的。”
我点支烟,抽起来。
“你没事吧,我是把你当前男友的,主要是,左边短头发那个,很帅。”
“加油。”
“我们打个赌吧,赌我今天能不能泡到他。”
“怎么赌?”
“我要是没泡到他,我今晚跟你走。”
“我是个惩罚?”
“帮个忙嘛,我需要动力。”
“那你要是成功了呢?”我问,“我默默祝福你俩?”
“你可以去泡寿星。”她指着一群女孩,我也没看清是哪个。“我去给你使把劲。”点点走过去,拿起桌上的纸帽子带到一个女孩的头上,冲着我使眼色。
寿星很漂亮,非常漂亮,仿佛河流中的紫罗兰。她对我笑下,我点点头,背过身饮酒。后来过来几个男孩和我摇色子赌酒,几轮下来越来越多人加入,我去了趟厕所位子就被占了。我有点晕,找个角落靠一会儿,清醒些发现那个姑娘坐我身旁。
“今天你过生日。”说完我就后悔了,我说礼物我都没准备。
“没关系,他们都没带,都跟你一样不认识我。”她说,“还有十分钟才算我生日。”
“那你多大?”
“现在是十七,还有,”她看看表,“还有十分钟。”
我掏出烟,问她抽吗。她表示不抽,她想抽黑猫,可店里没有。
“你是点点前男友?”
“她觉得是,才能算是。”
“她说你写书?我们出去透透气。”她没等我回答,就把我拉出包厢,“好多人我都不认识,我可不想一大帮人对我说生日快乐。还有几分钟?”
“九分钟。”
“把生日过了再进去,”她说,“我以前也喜欢看书。”
“看书是好事。”
“我以前喜欢郭敬明,你为什么写不过他?”
“不知道,”我退后两步,凝视着她,“你是宝宝?”
“你才知道?”
“其实我不知道,我在梦里见过你。”
“你们作家都是靠编梦调情的?”
“以前是的,但你我真的梦过,有一段时间天天梦到你。”
“为什么?我在你梦里什么样?”
“忘了,好几年前了,好像没有这么漂亮。”
“还有呢?”
“还有,我说你很好,不要伤害自己。”
“什么意思?”
“没什么,有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说你的,这个,比点点大多了,然后你说,她那是个坑。”
她笑了,贴着我的脸说:“为什么说到胸,你在梦里对我做什么了?”
“取悦你的事情。”
她闭上眼睛仿佛这六个字能带给她欢愉,睁开眼睛她问我几点了。
“十二点零三,哦,生日快乐,宝宝。”
她靠前吻了我,她舌头很软,介入我口中触到我牙齿后面的舌,待我把舌伸出时,她却离开了我的嘴。
“我十八岁的第一个吻。”
“我2007年最后一个吻。”
“别这么悲观,你晚上有事吗?”
“有,等着送你回家。”
她笑着摸摸我手背,说,“我得先回去看看,告诉大家我累了。”
“我就不去了吧。”
“出门右转第二个路口有家7-11,我一会儿就过去,”她走上楼,在高处对我说,“帮我买包黑猫。”
除了黑猫我又买听啤酒,我想起昨天和出版人同学的谈话,分手,相爱,死亡,真的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吗,和故事外的女孩相恋。一些同性或异性的恋人牵着手从路口经过。我的烟忘在V3,于是我抽起黑猫,丝丝薄荷香从喉咙穿过。我向着音乐的源头走回去。
两个服务生在清理包厢,party早已结束,服务生问我剩了两瓶酒,存谁的名字。
“宝宝,”我说,我接着打给点点,问她宝宝在哪。
“啊?她没跟你走吗?”
“没有。”
“那她就是跟别人走了,你放心,她总会跟个男人走的,今天是她十八岁生日。”
“好,我放心。你在哪?”
“我在车上,哎,你是谁?”
“什么?”
“有个男的在送我,我在问他。”
“不是短头发那个?”
“不是,不过这个也蛮帅的。”
“哦,那你是输了。”我说,“用我过去帮你吗,支走他?”
她低声重复:“我说啦,这个也蛮帅的。”
“明白。”
“你怎么办?”
“不知道,”我看看包厢里的残迹,“不知道。”
“你这次找我什么事?我一直没机会问。”
“没什么事,就看看你。”
“你现在对我印象一定特别坏。”她说,“我现在很差。”
“还好,我也一样差,刚还在幻想艳遇。”
“时机不对,你来的时候不好。我不是没想过你,经常会想起你,想起在我十六岁那年有个男朋友给我诗意和希望。但不是现在,我现在只想抱个人睡到明天。”她又低声说,“他真的很帅。”
“Haveagoodnight!”
“什么?”
“春宵愉快。”
服务生还在等我回复,抱着酒问我这些写谁的名字。我接过来看看,Johnewalkerkeepgoing.
“别溜达了,”我说,“打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