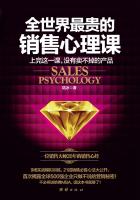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往故事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战全面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搞了7年的乡村建设工作自然就搞不下去了。他接到老朋友张群转来的蒋介石邀请自己去南京的电报。当时,国民党政府十分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于是就邀集了一些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到南京,在最高国务会议之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参议会”,其中亦有中共的代表参加,但大多数成员仍为国民党员。梁漱溟是作为无党派的社会贤达被邀请。这个“参议会”,就是后来在武汉成立又迁至重庆的“国民参政会”的前身。
梁漱溟立即关闭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风尘仆仆赶到了南京。但随着国民党军队“八·一三”抗战失利,日军长驱直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迁往武汉,梁漱溟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后为“参政员”)也随即到了武汉。沿途所见,一派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日,有的丢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有的不只自己逃难,还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对此,梁漱溟大失所望,对抗战的前途也很悲观。他想到自日本侵华后中共提出一系列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深得人心,并终于变成现实。现在国民党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样呢?百闻不如一见。于是,梁漱溟产生了去延安见见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念头。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和中共方面进行联系后,梁漱溟便奔赴延安。
梁漱溟到达延安,接待他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听了张闻天的介绍,梁漱溟才知道毛泽东是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张闻天对梁来延安表示欢迎,并为他设宴洗尘。张闻天说,毛泽东的习惯是白天休息,夜间办公,因此谈话便安排在夜间。
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的第一次谈话从下午6时至次日凌晨。时值冬天,延安气候严寒。6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地点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梁漱溟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他说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个人心中亦十分悲观,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梁表示这次来延安,就是向中共领袖讨教来的。
毛泽东听完梁漱溟的叙述,笑着回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上。毛泽东分析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
毛泽东话音刚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
“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毛泽东连声说。
时间已到后半夜,长谈告一段落。毛泽东很客气地说:“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续谈吧。”
“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说,“我先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
“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毛泽东说着,接过一本厚厚的书,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书名叫《乡村建设理论》。
第二天的谈话,也是从下午6点开始,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两人谈兴甚浓,欲罢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即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而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
梁漱溟当即争辩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两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还有兄友弟慕,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导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孝家庭,也孝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稳定、发展……”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长篇大论,然后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漱溟对此不以为然,他十分断然地说:“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看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
两人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在48年后的1986年秋天,毛泽东已经逝世10年,已经93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地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在与毛泽东的两夜长谈之后,梁漱溟还到延安各处参观。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很差,但到处生机勃勃,热气腾腾,其精神面貌与国统区有鲜明的区别。这都给梁漱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0余年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有了结果。1950年春天,梁漱溟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召,由重庆来到北京。梁漱溟认真思索了他一赴延安时与毛泽东发生的那场争论,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他在做了一番考察之后,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对自己做了一个总结。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梁漱溟的检讨和反省,虽然没有说清楚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但却在事实面前,承认了对于中国的前途问题,承认了毛泽东的认识是正确的,而自己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