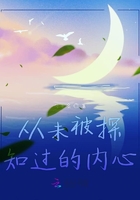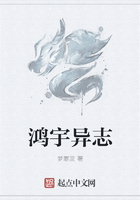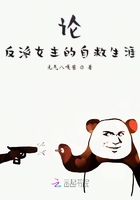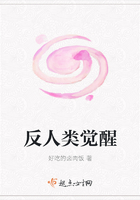集注“犹以为未足”一语,殊不稳妥。岂但以为未足哉!直是耳目心思之力,与形之方员、声之五音、天下治平之理,全然凑泊不着。规矩准绳因乎象,六律因乎数。圣人不于目求明,于耳求聪,而以吾心之能执象通数者为耳目之则。故规矩、六律之所自制,不得之耳目者而得之于心思,以通天下固有之象数,此以心而治耳目也。不忍人之政,上因天时,下因地利,中因人情。圣人不任心以求天下,而以天下固然之理顺之以为政,此以理而裁心思也。故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察迩言以执两端而用其中。岂有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之自用者哉!圣人用之而自不可胜用,乃以垂之后世而亦不可胜用,其理一,其效均也。
如谓先王为天下后世故,制此法度,若圣人之自为用者,一目击而方圆即定,一流耳而五音即定,一致思而仁即被于天下,则此圣人者,将如佛氏之观十方世界如掌中果,一按指而海印发光,一皆成就邪?言之无实,亦不祥矣。
既者,已事之词也;继者,遂事之词也。“已竭耳目心思”云者,劳已尽而绩未成也。“继之以规矩、准绳、六律、仁政”云者,言彼无益,而得此术以继之,乃以遂其所事也。双峰乃云“唯天下不能常有圣人,所以要继之[以]不忍人之政”。然则使天下而恒有圣人,则更不须此不忍人之政乎?是孔子既作,而伏羲之《易》,唐、虞之典,殷、周之礼,皆可焚矣!此老子“剖斗折衡”之绪论,释氏“黄叶止啼”、“火宅”、“化城”之唾余。奈何游圣贤之门,曾不揣而窃其旨也!、
人君之所不得于天下者,亦唯不亲、不治、不答以敬而已。其以莅下土而定邦交者,亦唯爱之、治之、礼之而已。仁、智、敬之皆反求矣,则亦更有何道之可反求也?只此三者,包括以尽。“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是总括上文以起下义。双峰乃云“上面三句包括未尽,‘皆’字说得阔”,徒为挑拨,了无实义,当亦未之思尔。
林氏所云“诸侯失德,巨室擅权”,自春秋时事。逮乎战国,天下之持权者又不在世卿而在游士矣。“不修其本,而遽欲胜之”,唯晋厉、鲁昭、齐简为然。战国时,列国之卿与公室争强弱者,仅见于田婴、韩朋,然亦终不能如三家、六卿之强逆也。以蟠根深固之魏冉,而范睢一言则救死之不暇。七国之贵公子者,劣以自保其富贵。安得有君欲胜之不能而取祸者哉?
孟子说“不得罪于巨室”,与周公“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意同,乃以收拾人心于忠厚仁慈之中,而非有称兵犯顺之王承宗、跋扈不恭之韩弘须为驾驭,不然则效安、史、滔、溉之为也。看孟子说“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则其云“为政不难”者,为施德教之令主言也。若唐宪宗一流恩、威两诎之君,本无德教,不足言矣。
《孟子》七篇,屡言兴王业之事,而未详所以定王业者。唯此一章是已得天下后经理措置之大业。所谓“为政”者,言得天下而为之也。得天下而为之,而先以尊尊、亲亲、重贤、敦故之道行之于庙堂之上,君臣一德,以旬宣而绥理之,勿使游谈之士持轻重以乱天下之耳目,则指臂相使,而令下如流水之原矣。当此之时,君臣一心德而天下待命焉,安所得擅权之巨室,杀之不能,纵之不可,须以处置遥持其生命乎?
裴晋公之进说也,挟韩弘、承宗之叛服以为辞,而云“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此等章疏,便是三代以下人习气。上失格君之道,下乖纯臣之义,只靠着祸福声势胁持其君以伸己意,而其文字流传,适以长藩镇之恶而不恤。以皇甫铸之不可使居相位为老臣者,不能正君心于早以杜其萌,则唯称引古谊,以明贵义、贱利、尊君子、远小人之大道;若其不听,无亦致位以去而已。今乃引叛臣之向背以怵其君,使之惧而庸吾言,则己志伸而国是定;即其不听,而抑有所操挟以白免于诛逐。其于“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之义,相去远矣。三代以下无大臣者,此也。奈何引孟子而同之!
粗疏就文字看,则有道之天似以理言,无道之天似以势言,实则不然。既皆曰“役”,则皆势矣。集注云“理势之当然”,势之当然者,又岂非理哉!所以庆源、双峰从理势上归到理去,已极分明。
“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小役大,弱役强”, 势也。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
大德大贤宜为小德小贤之主,理所当尊,尊无歉也。小德小贤宜听大德大贤之所役,理所当卑,卑斯安也。而因以成乎天子治方伯、方伯治诸侯、诸侯治卿大夫之势。势无不顺也。
若夫大之役夫小,强之役夫弱,非其德其贤之宜强宜大,而乘势以处乎尊,固非理也。然而弱小之德与贤既无以异于强大,借复以其蕞尔之土、一割之力,妄逞其志欲,将以陨其宗社而死亡俘虏其人民,又岂理哉!故以无道之弱小,而无强大者以为之统,则竞争无已,戕杀相寻,虽欲若无道之天下尚得以成其相役之势而不能。则弱小固受制于强大,以戢其糜烂鼎沸之毒。而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已。
曹操曰:“使天下无孤,则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自操言之,固为欺凌蔑上之语,若从旁旷观,又岂不诚然邪?是虽不得谓强大之役人为理之当然,而实不得谓弱小之役于人非理之所不可过也。故本文云:“小役大,弱役强,天也。”自小弱言之,当役而役,岂非理哉!是非有道之天唯理,而无道之天唯势,亦明矣。
双峰以势属之气,其说亦可通。然既云天,则更不可析气而别言之。天者,所以张主纲维是气者也。理以治气,气所受成,斯谓之天。理与气元不可分作两截。若以此之言气为就气运之一泰一否、一清一浊者而言,则气之清以泰者,其可孤谓之理而非气乎?
有道、无道,莫非气也,此气运、风气之气。则莫不成乎其势也。气之成乎治之理者为有道,成乎乱之理者为无道。均成其理,则均成乎势矣。故曰:“斯二者,天也。”使谓泰有理而非气,否但气而无理,则否无卦德矣。是双峰之分有道为理,无道为气,其失明矣。
若使气之成乎乱者而遂无理,则应当无道之天下,直无一定之役,人自为政,一彼一此,不至相啖食垂尽而不止矣。其必如此以役也,即理也。如疟之有信,岂非有必然之理哉!无理之气,天地之间即或有之,要俄顷而起,俄顷而灭。此大乱之极,如刘渊、石勒、敬瑭、知远。百年而不返,则天地其不立矣!
理与气不相离,而势因理成,不但因气。气到纷乱时,如飘风(飘)[骤]雨,起灭聚散,回旋来去,无有定方,又安所得势哉!凡言势者,皆顺而不逆之谓也;从高趋卑,从大包小,不容违阻之谓也。夫然,又安往而非理乎?知理势不可以两截沟分,则双峰之言气,亦徒添蛇足而已。
言理势者,犹言理之势也,犹凡言理气者,谓理之气也。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故其始之有理,即于气上见理;迨已得理,则自然成势,又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
双峰错处,在看理作一物事,有辙迹,与“道”字同解。道虽广大,然尚可见,尚可守,未尝无一成之侧。故云“天下有道”,不可云“天下有理”。则天下无道之非无理,明矣。
道者,一定之理也。于理上加“一定”二字方是道。乃须云“一定之理”,则是理有一定者而不尽于一定。气不定,则理亦无定也。理是随在分派位置得底。道则不然,现成之路,唯人率循而已。故弱小者可反无道之理为有道之理,而当其未足有为,则逆之而亡也。孟子于此,看得“势”字精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曰“天”。进可以兴王,而退可以保国,总将理势作一合说。曲为分析,失其旨矣。
安其危,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自是三项人。国削兵衄,犹自偷一日之安者,“安其危”也。能为国家之灾害者,而彼反以为利,如虞公之璧马,平原君之上党,祸所自伏,而偏受其饵者,“利其灾”也。荒淫暴虐,为酒池、肉林、琼林、大盈者,“乐其所以亡”也。
不仁者之有此三者,亦各有所因。昏惰而不能自强于政治,故“安其危”。贪利乐祸,小有才而忮害无已,故“利其灾”。嗜欲蔽锢,沉湎而不知反,故“乐其所以亡”。三者有一,即不可与言矣。
如宋理宗亦无甚利灾、乐亡之事,而但居危若安,直是鼓舞警戒他不动。梁武帝未尝安危、乐亡,乃幸侯景之反覆,以希非望之利,故虽自忧其且败而纳景。首祸之心,终不自戢,则人言又何从而人?若唐玄宗之晚节,未尝安危而利灾也,特以沉湎酒色,而卒致丧败,则虽知张九龄之忠,而终幸李林甫之能宽假以征声逐色之岁月,故言之而必不听。
三者有一,则必至于亡国败家。而若楚怀王、秦二世、隋炀帝、宋徽宗,则兼之者。以其昏惰安危贪忮利灾沉溺嗜欲乐亡者而言之,则统为不仁。然不仁者未必皆合有此三者也。双峰归重末句,自未分晓。其意以为唯荒淫暴虐者,则与集注“心不存”之说相为吻合。乃集注“心不存则无以辨于存亡之着”一语,亦抬起此不仁者太高。若论到存心上,则中材之主能保其国家者,若问他仁义之心在腔子里与否,则无论“三月不违”,即日月一至,乃至一念之分明不昧,亦不可得。然而以免败亡而有余者,则未能仁而犹不至于不仁,尚可与言也。人而谓之不仁,岂但不能存其心哉,直已丧其心矣!
心不存者,谓仁义之心不存也;丧其心者,并知觉运动之心而亦丧也。昏惰、贪忮、沉溺之人,他耳目日鼻、精神血气,只堆垛向那一边去,如醉相似,故君子终不可与言,弗能为益而只以自辱。若仅不能存其心,则太甲、成王之蚤岁固然,正伊尹、周公陈善责难之几也,何遽云不可与言邪?
“反身而诚”,与《大学》“诚意”“诚”字,实有不同处,不与分别,则了不知“思诚”之实际。“诚其意”,只在意上说,此外有正心,有修身。修身治外而诚意治内,正心治静而诚意治动。在意发处说诚,只是“思诚”一节工夫。若“反身而诚”,则通动静、合外内之全德也。静而戒惧于不睹不闻,使此理之森森然在吾心者,诚也。动而慎于隐微,使此理随发处一直充满,无欠缺于意之初终者,诚也。外而以好以恶,以言以行,乃至加于家国天下,使此理洋溢周遍,无不足用于身者,诚也。三者一之弗至,则反身而不诚也。
唯其然,故知此之言诚者,无对之词也。必求其反,则《中庸》之所云“不诚无物”者止矣,而终不可以欺与伪与之相对也。朱子曰:“不曾亏欠了他底。”又曰:“说仁时恐犹有不仁处,说义时恐犹有不义处,便须着思有以实之。”但依此数语,根究体验,自不为俗解所惑矣。
大学分心分意于动静,而各为一条目,故于“诚其意”者,说个“毋自欺”。以心之欲正者居静而为主,意之感物而有差别者居动而为宾,故立心为主,而以心之正者治意,使意从心,而毋以乍起之非几凌夺其心,故曰“毋自欺”,外不欺内、宾不欺主之谓也。
今此通天人而言诚,可云“思诚者”人不欺天,而“诚者天之道”,又将谓天下谁欺邪?故虽有诚不诚之分,而无欺伪之防。诚不诚之分者,一实有之,一实无之;一实全之,一实欠之。了然此有无、全欠之在天下,固不容有欺而当戒矣。
“诚者天之道也”,天固然其无伪矣。然以实思之,天其可以无伪言乎?本无所谓伪,则不得言不伪;如天有曰,其可言此日非伪日乎?乃不得言不伪,而可言其道曰“诚”;本无所谓伪,则亦无有不伪;本无伪曰,故此曰更非不伪。乃无有不伪,而必有其诚。则诚者非但无伪之谓,则固不可云“无伪者天之道”也,其可云“思无伪者人之道”乎?
说到一个“诚”字,是极顶字,更无一字可以代释,更无一语可以反形,尽天下之善而皆有之谓也,通吾身、心、意、知而无不一于善之谓也。若但无伪,正未可以言诚。曰“有恒”。故思诚者,择善固执之功,以学、问、思、辨、笃行也。己百己千而弗措,要以肖天之行,尽人之才,流动充满于万殊,达于变化而不息,非但存真去伪、戒欺求慊之足以当之也。尽天地只是个诚,尽圣贤学问只是个思诚。即是“皇建其有极”,即是二殊五实合撰而为一。
孟子言“皆备”,即是天道;言“扩充”,即是人道。在圣学固不屑与乡原之似忠信、似廉洁者为对,在王道亦不屑与五伯之假仁假义者为对。学者先须识得此字,然后见处真,立处大,可有至百步之力,而亦不昧于中百步之巧。若将此“诚”字降一格,使与“欺”字“伪”字作对,则言必信、行必果,磋径然之小人便是配天之至诚矣。
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大段事,只当得此“思诚”一“思”字,曰“命”、曰“性”、曰“道”、曰“教”,无不受统于此一“诚”字。于此不察,其引人人迷津者不小。广平引《大学》“欲诚先致”释明善、诚身之序,自是不谬,以致知、诚意是思诚者知行分界大段处也。若庆源死认诚意为诚身,而孤责之隐微之无欺,则执一砾石而谓太山之尽于是,亦乌知其涯际哉!
文王当商命未改之时,犹然受商之铁钺以专征,故无图天下之心,而后为大公无私。若孟子所以期当时之侯王者,则异是。周德已讫,而民之憔悴甚矣。天命须是教有所归,斯民须是令之有主,此亦有广土众民者义之所不得辞。则但行文王之政,不必心文王之心,而已无愧于文王。
况乎汉高之王汉中,秦已亡而天下裂,义帝之在郴南,初未尝正一日君臣,如夏、商世德相承之天子,为汉之所必戴也。至项羽之稔恶已盈,固不足以为盟主,分汉王于汉中,非所宜顺受之命。使汉君臣不以天下为图,徒保守一隅,养民致贤而一无所为,为之,则一吴芮、尉佗而已矣。集注以私罪汉,未合于时措之宜也。
到廓然大公处,却在己在人,更不须立町畦,自贻胸中渣滓。上审天命,下察人心,天理所宜,无嫌可避。使文王而当七雄、秦、项之际,上无可服事之故主,下无可推让之邻国,又岂得不以天命不可旷、民望不可违为大公至正之道哉!
七雄之不仁,项羽之不义,既恶剧于崇、密而必不可北面事之;苟有其德,允当其位,而当此两不相下之势,如项羽之不并天下不休者,又岂如四海义安,仅保一方之三苗可舞干而格?则以天下为己任者,“勿贰尔心”,而夙夜以期乎必济,正以其身为天下用,而不徇小名小义以自私。藉令汉高而忘天下也,膜视此中国糜烂瓜分于项氏之手,又岂文王之所忍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