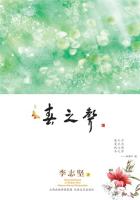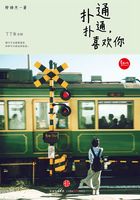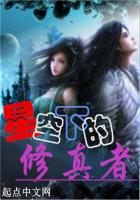时间也就这样过去。去年八九月间,他委托他的老伴告诉我的儿子,要我到医院里去看他。我十分了解他的心情:这是要同我最后诀别了。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同儿子到了他住的医院里。病房同中南海他的住房同样宽敞高大,但我的心情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同那一次进中南海相比,我这一次是来同老友诀别的。乔木仰面躺在病床上,嘴里吸着氧气。床旁还有一些点滴用的器械。他看到我来了,显得有点儿激动,抓住我的手,久久不松开。看来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握老友的手了。但是,他神态是安详的,神志是清明的,一点儿没有痛苦的表情。他仍然同平常一样慢声慢气地说着话。他曾在《人物》杂志上读过我那《留德十年》的一些篇章。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又忽然想了起来,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我此时此刻百感交集,我答应他全书出版后,一定送他一本。我明知道这只不过是空洞的谎言。这种空洞萦绕在我耳旁,使我自己都毛骨悚然。然而我不说这个又能说些什么呢?
这是我同乔木最后一次见面。过了不久,他就离开了人间。按照中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的做法,《留德十年》出版以后,我应当到他的坟上焚烧一本,算是送给他那在天之灵。然而,遵照乔木的遗嘱,他的骨灰都已撒到他革命的地方了,连一个骨灰盒都没有留下。他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然而,对我这后死者来说,却是极难排遣的。我面对这一本小书,泪眼模糊,魂断神销。
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上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六十年的宦海风波,他不能无所感受,但是他对我半点儿也没有流露过。他大概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说了也是白说。在他生前,大陆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为“左王”,另外一位同志同他并列,称为“左后”。我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
我同乔木相交六十年。在他生前,对他我有意回避,绝少主动同他接近。这是我的生性使然,无法改变。他逝世后这一年多以来,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倒常常想到他。我像老牛反刍一样,回味我们六十年交往的过程,顿生知己之感。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乔木是了解我的。有知己之感是件好事。然而它却加浓了我的怀念和悲哀。这就难说是好是坏了。
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在人世间,后死者的处境是并不美妙的,年岁越大,先他而走的亲友越多,怀念与悲思在他心中的积淀也就越来越厚,厚到令人难以承担的程度。何况我又是一个感情常常超过需要的人,我心里这一份负担就显得更重。乔木的死,无疑又在我的心灵中增加了一份极为沉重的负担。我有没有办法摆脱这一份负担呢?我自己说不出。我怅望窗外皑皑的白雪,我想得很远,很远。
1993年11月28日凌晨
悼组缃
组缃毕竟还是离开我们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最近几年来,他曾几次进出医院,有时候十分危险,然而他都逢凶化吉,走出了医院。我又能在池塘边上看到一个戴儿童遮阳帽的老人,坐在木头椅子上,欣赏湖光树影。
他前不久又进了医院。我仍然做着同样的梦,希望他能再一次化险为夷,等到春暖花开时,再一次坐在木椅子上,为朗润园增添一景。然而,这一次我的希望落了空。组缃离开了我们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对我个人来说,我失掉了一个有六十多年友谊的老友。偌大一个风光旖旎的朗润园,杨柳如故,湖水如故,众多的贤俊依然灿如列星,为我国的文教事业增添光彩。然而却少了一个人,一个平凡又不平凡的老人。我感到空虚寂寞,名园有灵,也会感到空虚与寂寞的。
距今六十四年以前,在30年代的第一年,我就认识了组缃,当时我们都在清华大学读书。岁数相差三岁,级别相差两级,又不是一个系。然而,不知怎么一来,我们竟认识了,而且成了好友。当时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林庚和李长之,可以说是清华园“四剑客”。大概我们都是所谓“文学青年”,都爱好舞笔弄墨,共同的爱好把我们聚拢在一起来了。我读的虽然是外国语文系,但曾旁听过朱自清先生和俞平伯先生的课。我们“四剑客”大概都偷听过当时名噪一时的女作家谢冰心先生的课和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先生的课,结果被冰心先生板着面孔赶了出来。和郑振铎先生,我们却交上了朋友。他同巴金和靳以共同创办了《文学季刊》,我们都成了编委或特约撰稿人,我们的名字堂而皇之地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郑先生这种没有一点儿教授架子,决不歧视小字辈的高风亮节,我曾在纪念他的文章中谈到。我们曾联袂到今天北京大学小东门里他的住处访问过他,对他那插架的宝书曾狠狠地羡慕过一阵。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可惜长之和组缃已先后谢世,能够回忆的只剩下我同林庚两人了。
我们“四剑客”是常常会面的,有时候在荷花池旁,有时候在林荫道上,更多的时候是在某一个人的宿舍里。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的岁数最小,还不到二十岁,正是幻想特多,不知天高地厚,仿佛前面的路上全铺满了玫瑰花的年龄。我们放言高论,无话不谈,“语不惊人死不休”。个个都吹自己的文章写得好,不是梦笔生花,就是神来之笔。林庚早晨初醒,看到风吹帐动,立即写了两句话:
破晓时天旁的水声
深林中老虎的眼睛
当天就念给我们听,眉飞色舞,极为得意。他的一篇诗稿上有一个“袭”字,看上去像是“聋”字。长之立即把这个“聋”字据为己有。原诗是“袭来了什么什么”,现在成了“聋来了什么什么”。他认为,有此一个“聋”字而境界全出了。
我们会面的地方,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工字厅。这是一座老式建筑,里面回廊曲径,花木蓊郁,后临荷塘,那一个有名的写着“水木清华”四个大字的匾,就挂在工字厅后面。这里房间很多,数也数不清。中间有一座大厅,按现在的标准来说,也不算太大。厅里旧木家具,在薄暗中有时闪出一点光芒。这是一个非常清静的地方,平常很少有人到这里来。对我们“四剑客”来说,这里却是侃大山(当时还没有这个词儿)的理想的地方。我记得茅盾《子夜》出版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又凑到一起,来到这里,大侃《子夜》。意见大体上分为两派:否定与肯定。我属于前者,组缃属于后者。我觉得,茅盾的文章死板、机械,没有鲁迅那种灵气。组缃则说,《子夜》结构闳大,气象万千。这样的辩论向来不会有结果的。不过是每个人淋漓尽致地发表了意见以后,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又谈起别的问题来了。
组缃上中学时就结了婚。家境大概颇为富裕,上清华时,把家眷也带了来。现在听说中国留学生可以带夫人出国,名曰伴读。当时是没有这个说法的。然而组缃的所作所为不正是“伴读”吗?组缃真可谓“超前”了。有了家眷,就不能住在校内学生宿舍里。他在清华附近西柳村租了几间房子,全家住在那里。我曾同林庚和长之去看过他。除了夫人以外,还有一个三四岁的女孩,小名叫小鸠子,是非常聪慧可爱的孩子。去年下半年,我去看组缃,小鸠子正从四川赶回北京来陪伴父亲。她现在也已六十多岁,非复当日的小女孩了。我叫了一声:“小鸠子!”组缃笑着说:“现在已经是老鸠子了。”相对一笑,时间流逝得竟是如此迅速,我也不禁“惊呼热中肠”了。
清华毕业后,我们“四剑客”天南海北,在茫茫的赤县神州,在更茫茫的番邦异域,各奔前程。为了糊口,为了养家,在花花世界中,摸爬滚打,历尽苦难,在心灵上留下了累累伤痕。我们各自怀着对对方的忆念,在寂寞中,在沉默中,等待着,等待着。一直等到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组缃和林庚又都来到了北大,我们这“三剑客”在暌离二十年后又在燕园聚首了。此时我们都已成了中年人,家事、校事、国事,事事萦心。当年的少年锐气已经磨掉了不少,非复昔日之狂纵。燕园虽秀美,但独缺少一个工字厅,缺少一个水木清华。我们平常难得见一次面,见面大都是在校内外召开的花样繁多的会议上。一见面,大家哈哈一笑,个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也。
时光是超乎物外的,它根本不管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从无始至无终,始终是狂奔不息。一转瞬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其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中国的老知识分子无不有切肤之痛,大家心照不宣,用不着再说了。我同组缃在牛棚中做过“棚友”,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终于都离开了中年,转入老年,进而进入耄耋之年。不但青年的锐气消磨精光,中年的什么气也所余无几,只剩下了一团暮气了。幸好我们这清华园“三剑客”(长之早已离开了人间)并没有颓唐不振,仍然在各自的领域里辛勤耕耘,虽非“志在千里”,却也还能“日暮行雨,春深著花”,多少都有所建树,差堪自慰而已。
前几年,我同组缃的共同的清华老友胡乔木,曾几次对我说:“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我颇讶其伤感。前年他来北大参加一个什么会。会结束后,我陪他去看了林庚。他执意要看一看组缃,说他俩在清华时曾共同搞过地下革命活动。我于是从林庚家打电话给组缃,打了好久,没有人接。并非离家外出,想是高卧未起。不管怎样,组缃和乔木至终也没能再见上一面。乔木先离开了人间,现在组缃也走了。回思乔木说的那一句话,字字是真理,哪里是什么感伤!我却是乐观得有点儿可笑了。
我默默地接受了这个教训,赶在组缃去世之前,想亡羊补牢一番。去年我邀集了几个最老的朋友:组缃、恭三(邓广铭)、林庚、周一良等小聚了一次。大家都一致认为,老友们的兴致极高,难得浮生一夕乐。但在觥筹交错中,我不禁想到了两个人:一是长之,一是乔木,清华“剑客”于今飘零成“广陵散”矣。我本来想今年再聚一次,被邀请者范围再扩大一点。哪里想到,如果再相聚的话,又少了一个人:组缃。暮年老友见一面真也不容易呀!
不管我还能活上多少年,我现在走的反正是人生最后一段路程。最近若干年来,我以忧患余生,渐渐地成了陶渊明的信徒。他那形神相赠的诗,我深深服膺。我想努力做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我想努力做到宋人词中所说的“悲欢离合总无情”。我觉得,自己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我对这花花世界确已看透,名缰利索对我的控制已经微乎其微。然而一遇到伤心之事,我还不能“总无情”,而是深深动情,组缃之死就是一个例子。生而为人,孰能无情,一个“情”字不就是人之所异于禽兽者的那一点“几稀”吗?
有一件事却让我触目惊心。我舞笔弄墨之十多年于兹矣。前期和中期写的东西,不管内容如何,不管技巧如何,悼念的文章是极为稀见的。然而最近几年来,这类文章却逐渐多了起来。最初我没有理会。一旦理会到了,不禁心惊胆战。一个人到了老年,如果能活得长一点,当然不能说是坏事。但是,身旁的老友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自己,宛如郑板桥诗所说的“删繁就简三秋树”,如果“简”到只剩下自己这一个老枝,岂不大可哀哉!一个常常要写悼念文章的人,距离别人为自己写悼念文章,大概也为期不远了。一想到这一点,即使自己真能“不喜亦不惧”,难道就能无动于衷吗?
但是,眼前我并不消极,也不颓唐,我决不会自寻“安乐死”的。看样子我还能活上若干年的,我耳不聋,眼稍昏,抬腿就是十里八里。王济夫同志说我是“奇迹”,他的话有点儿道理。我计划要做的事,其数量和繁重程度,连一些青年或中年人都会望而却步,借用冯友兰先生的话,我是“欲罢不能”。天生是辛劳的命,奈之何哉!看来悼念文章我还是要写下去的。我并没有老友臧克家要活到一百二十岁那样的雄心壮志,退而求其次,活到九十多,大概不成问题。我还有多少悼念文章要写呀,恐怕没有人敢说了。
1994年2月2日
悼许国璋先生
小保姆告诉我,北京外国语大学来了电话,说许国璋教授去世了。我不禁“哎哟”了一声。我这种不寻常的惊呼声,在过去相同的场合下是从来没有过的。它一方面表现了这件事对我打击之剧烈,另一方面其背后还蕴含着一种极其深沉的悲哀,有如被雷击一般,是事前绝对没有想到的,我只有惊呼“哎哟”了。
我同国璋,不能算是最老的朋友。但是,屈指算来,我们相识也已有将近半个世纪了。在解放初期那种狂热的开会的热潮中,我们常常在各种各样的会上相遇。会虽然是各种各样,但大体上离不开外国语言和文学。我们亦不是一个行当,他是搞英语的,我搞的则是印度和中亚古代语言。但因为同属于外字号,所以就有了相会的机会。我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以后在清华,虽云专修德语,实际上所有的课程都用英语来进行,因此我对英语也不敢说是外行,又因此对国璋的英语造诣也具有能了解的资格。英语界的同行们对他的英语造诣之高,无不钦佩。但是,他在这一方面绝无骄矜之气。他待人接物,一片淳真,朴实,诚恳,谦逊,但也并不故做谦逊状,说话实事求是,决不忸怩作态。因此,他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毕生难忘的印象。
到了那一个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他理所当然地在劫难逃。风闻他被打成了外院“洋三家村”的大老板。中国人作诗词,讲究对偶,“四人帮”一伙虽然胸无点墨,我们老祖宗这个遗产,他们却忠诚地继承下来了,既有“土三家村”,必有“洋三家村”。国璋等三个外院著名的英美语言文学的教授,适逢其会,叨蒙垂青,于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洋三家村”就出现在大字报上了。大家都知道,“土三家村”是“十年浩劫”的直接导火线。本来不存在的事实却被具有“天眼通”、“天耳通”的“四人帮”及其徒子徒孙们“炒”成了“事实”,搞得乌烟瘴气,寰宇闻名。中一变而为外,土一变而为洋,当时崇洋媚外,罪大恶极——其实“四人帮”一伙是在灵魂深处最崇洋媚外的——“土三家村”十恶不赦,而“洋三家村”则必然是万恶不赦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璋所受的皮肉之苦,以及精神上的折磨,概可想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