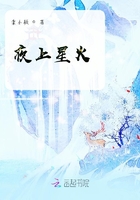马上的男子轻扯缰绳,头戴战甲的马儿稳稳停下脚步,焰红的夕阳将他绝美的五官勾勒,仿佛从万丈光芒中穿越而来,睫毛上都沾染了点滴韫色。
我以为像苏景这种在玉门关一待就是十多年,应该是身材魁梧,行动举止不拘小节,满脸胡子拉碴的样子,没想到却是这样的气质出众,神情不凡。
听说苏景身边有一位女将士,名为赤练,武功高强,擅长使用鞭子与易容之术,巾帼不让须眉,一点儿也不输给军营里的男将军。
面前这位杀气凝重的绯衣女子,长相张扬妖艳,眼神犀利逼人,大概就是赤炼了吧。
江皓宇的一干手下们见到苏景的马驾与蓝旌旗,纷纷停止了追势,面面相觑着,大眼看小眼,猜测我和这些人是否有关系,也有可能是被赤练的眼神所摄,一个也不敢上前造次。
我夹在这两拨人中间,赤练的银鞭就挡在我面前,也不敢上前一步。
我朝马背上的苏景欠身说道:“将军救命,这些人的主子欺负良家妇女,被我与一位朋友所阻,他们的主子气不过,便叫人在巷子里拦我们,我和那位朋友走散,他们仍然不依不饶,还望将军出手相救。”
如果是陈止,我倒可以大方说出其实我的身份,但是苏景呢,他和苏洵不太对付,虽然我和苏洵也没到同气连枝的地步,神仙斗法,难免可能会伤了我这个小兵小卒。
万一苏景觉得在玉门关吃了那么多年的风沙,报复苏洵暂时无望,退而求其次来报复我,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我觉得还是不要自报家门为好。
苏景冷睨地扫了我一眼,紧盯着我的脸过了好半晌,眼中有不知名的东西一闪而过,转而唇边溢出一抹淡淡浅笑,神色由深邃转为玩味十足,把弄着手中的马缰。
我以为他要转身拍拍屁股离去,谁知他却兴趣盎然道:“赤练,迎敌。”
那位叫赤练的绯衣女子先是不可思议地看了苏景一眼,想来她家王爷是第一次替人出头,随即不辱使命地冷眼瞧着我身后那些人。
我只觉得一道红影宛如闪电从那些人中间闪过,还没看清是怎么出手的,伴随几身杀猪般的惨叫,个个倒地哀嚎着,赤练已经回到方才停留的位置,手中的银鞭甚至都没挥出去过。
最惨的还是那个家丁,早上被揍了一顿,现在又被揍了一顿,打得他连气都不敢喘了,看得我都疼。
那些人在地上滚了几圈,衣服沾了很多黄土,狼狈万分,然后迅速爬起来,见鬼似的地逃离去,连脚上的鞋子掉了一只也顾不得了,也许赤练对他们来说比鬼还可怕百倍千倍,生怕慢了还会被揍,刚才对我穷追不舍时都达不到这种速度,爆发力甚是惊人,求生欲望也很强烈。
我目瞪口呆看着他们连滚带爬地四下逃蹿,如果今日不是我在此碰上苏景,恐怕此刻被打得屁滚尿流的就是我了吧。
苏景像个局外人在马背上看完全过程,悠然道:“有趣。”
随即调转马儿,继续往前走着,我记得平阳王府邸是在皇宫以西,他们一行人大概是准备回府了吧。
还没来得及表示谢意,他们已经走远,留下稀稀疏疏几个背影。
我朝他们的背影大喊着:“若有机会,定当报答。”也不管他们能否听到。
他们渐行渐远,紫旌旗在风中翻飞着,像只紫色的大鸟,最后在小坡拐弯处完全消失不见了。
不知那句“有趣”,是指那些落荒而逃的人,还是指我。
我心里担心着太平的安危,没有细想,沿途找人问了东街的位置,马上起程赶过去。
我一边赶路,夕阳也一分一分落下去。
大宅外面的门上点着几个风灯,天上零零落落散着几颗星子,像是夏天河边的萤火虫,月亮还隐藏在深蓝色的云层之后。
东街街市两排幌线上挂着一列紫红的南瓜灯,大元农商并重,上京城的商业更是繁荣不衰,不远万里的别国人士也经常出没,商人到了大半夜还在行路的是平常得再不能平常的事,,这是为晚归的商旅还有夜游的行人照明用的。
太平站在一顶硕大的南瓜灯下,踮起脚尖站在勾栏上,两只手像壁虎爬树似的粘在拦柱上,撑着身子极目四望看着远处的道路,连我大摇大摆走近她身边也浑然不知。
“看什么呢?我也想瞧瞧。”我贴近她的脑后道。
我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边看,嘴角还带着花儿一样的笑意,所以学着她的样子也跟着看向远处,万家灯火通明,灯火无法触及的地方黑乎乎一片,可瞧不出什么别的东西来。
“哎呀,皇嫂你吓死我了。”太平惊得跳了一跳,差点从栏上摔下去,回头愤怒地看着我。
我拨拨地上的落叶,说:“是你一心都在看着别的地方,连我来了都没发现。你到底是在看什么呢,看得这么出神。”
夜风凉爽,吹散了街道上的热气,幌线上的南瓜灯被吹得微微晃动,笼里的烛火像盛在摇篮里轻轻荡漾着,地上的影子也跟着一晃一晃的时明时暗。
太平痴痴地笑着,“我甩开那些人之后,就在这里等着你,你猜我遇见了谁?”
看她一脸喜色滋滋,少女怀春的样子,我故意地说:“不会是遇上了采花大盗吧。”
“皇嫂你真厉害,一猜就着。”太平简直激动得击掌。
我记得之前父亲提过这个人,简直是良家妇女的噩梦,人人叫苦连天,可是官府都拿他没办法,上京衙门卧虎藏龙,让我有点怀疑政府部门的办事能力,或者那位采花贼成功打入了官府内部,所以才能在辣手摧花那么多次后还能法外逍遥。
在普通人看来,我们是谦谦公子,但凡遇上一个资深的,就伪装不下去了。
那采花贼阅人无数,轻易识破我们的女子身份不足为奇。
莫不是太平涉世未深,而那采花贼又是情场高手,三言两语之间就获得她芳心暗许。
我有点担忧地说:“那你还笑得这么花痴,难道你喜欢上他了。”
她这个反应真是不太正常,要真是如此,被她老兄苏洵知道,治我个看管不力之罪,我不得连脑袋都被削了。
太平不理会我的话,拉着我的手激动地道:“千钧一发之际,你猜我又遇上了谁?”
“白季尘?”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太平朝我投来崇拜的眼神,眼睛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明亮水灵,她犹如遇上知音故人,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我记得都统府是在东俞城以东,白季尘今日来了锁仙居,想要回都统府也只有经过东街这条路。
也只有白季尘有比较大出手相救的可能性,若是不知情者,看到采花贼想对太平无礼,只能是另外一则故事:两个大老爷们罔顾人论,当街嘻戏打闹,严重影响上京市容。
“他当时从马上下来,一把就将我拉到身后去了,就像这样······”
太平耳提面命地拉着我的手环上她的腰,模拟白季尘飞身救她的场景,之后旋转了几圈,旋啊旋,南瓜灯下,袍袖飞扬,像两只不断飞舞的化蝶,我无法身临其境体验那种带着幸福气息的感受,只觉得一阵阵天旋地转,真是要将我在锁仙居吃的东西都给吐出来。
靠在灯柱下缓和好久,眼前一圈一圈的星星才渐渐消去。
我喘着气道:“那我再猜猜看你接下会说什么。”我深深地看了她一眼,“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
太平两个食指在身前蜻蜓点水地点着,有点委屈巴巴地说:“他之前百般戏弄我,这次本来只想跟他道谢的,都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冲上去将采花贼揍了一顿,一边追一边打,把采花贼打到东俞县官那里去了。”
这小姑娘春心大动了还不自知,我安抚似的摸摸她的脑袋,心里却觉得白季尘是个不错的人才,但不是个适合她的驸马,即使白季尘看起来就像吃软饭的,但也不能单看外表就否认了他掌管八万都卫的事实。
白季尘成天混在女人堆里,跟他洁身自好又古板的父亲白齐完全相反,在上京中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风流韵事缠身,花楼酒楼少不了他的身影,连上朝都比不上寻花问柳重要,府中养着的舞姬都比苏洵后宫的女人多,虽然苏洵身边的女人并不多。
经过初步观察白季尘应该是喜欢温婉柔顺类型的,太平性格坦率纯真,是个耿直善良而且脾气火爆的性子,也只有苏洵这个哥哥才能降得住她。
陈止倒是个不错的选择,既不吃喝赌搏也不拈花惹草,也是仪表堂堂,主要是不用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扫除那些红粉知己,估计锁仙居一半以上的姑娘,都不会不识白季尘的大名。
锁仙居不仅姑娘长得水灵,厨艺也堪称一流,主要是酿得一手莲花白酒,在微热的初夏再搭上几道凉菜,不知不觉吃了一肚子。
今早起来,手脚冰凉冰凉的,腹中隐隐有些难受,像是暴风雨前的看似风平浪静其实暗藏猫腻。
这才记起小日子差不多也就在这几天,昨日一时兴起,在锁仙居喝了那么多冷酒,这个微微疼痛的前兆有点不太好。
阿娘生我的时候历经千辛万苦,听家里的老人说我出生时骨瘦如柴,比小猫咪还瘦小,能不能养活还是个不定数,还好父亲弥补了一点先天不足,才避免许多后天畸形,但每个月那几天也是难熬。
果不其然,还真说来就来了。
越到正午时分,肚子越发疼痛,稍有用力,便血流如注,仿佛决堤似的,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连带着头也开始眩晕,不得不弯下身以求缓解。
程妈妈说等我以后嫁人生子就不会闹小日子了,至于是个什么原理,她支支吾吾了半天叶没说清楚。
话虽如此,她还是将老花姜片连着其它东西一并带进宫来。
有所好转之后,我起身前往未央宫,找程妈妈要一些老花姜镇痛。
一路抵达未央宫,在含元殿前停下,庭前的杜鹃花开得娇艳欲滴,红的粉的都有,蝴蝶围着起舞翩翩,重重花瓣压下来,把细嫩的腰枝都压弯了。
后殿的葡萄藤长势迅猛,藤末处挂着细小葫芦串似的花苞,我打算再过些日子搭个小棚,秋天时,,在藤下的竹椅乘凉看星星,还有紫绿紫绿的葡萄串。
程妈妈恰好从含元殿里出来,即使我不在的日子里,未央宫在她的打理下井然有序,宫娥们没有出现偷懒的现象。
“黎儿。”程妈妈唤了声我的乳名,对此时站在此地的我显得有些疑惑。
一个月以来,金华殿的宫娥们叫我林许,苏洵整天丑丫头来丑丫头去,差点都要忘了我本名。
“程妈妈。”我笑着边说边走上前去,像以前一样自然地拉起她的手,谁知她的手却包着一层纱布,包成跟两个粽子一样。
我着急地说:“程妈妈,你的手?”
程妈妈的手往袖中缩了缩,不同于往常的面露尴尬之色道:“前天不小心打翻了汤锅,被烫着了,也没严重,是小菊太过小题大做非把我包扎成这样。”
小菊是我入驻未央宫的接待宫娥,大概十三、十四岁左右,为人老实本分,胆小安静,见了我都是低着头走的。
日光穿过稀稀疏疏的枝叶打在脸上,既刺目又难受,晃得我更加头晕眼花,我扶着程妈妈的胳膊,打算进殿去休息,顺便谈谈正事。
“皇后娘娘请留步。”一个小宫娥跌跌撞撞朝我跑来,夹着稚嫩的嗓子委屈道:“皇后娘娘可要为我们未央宫的人做主。”
程妈妈和我的步子一滞,她略显得有些不安,急冲冲跑来的正是小菊,这么莽撞的她我还是第一次遇见,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小菊,你胡说些什么,还不赶紧退下。”程妈妈气急地说道,挣开我的手三步并作两走到小菊面前,“平日里的规矩都学到哪里去了。”
小菊扑通一声跪下,重重磕了个响头,啜泣道:“请皇后娘娘为未央宫的婢子们做主。”
我没想到她竟会行此大礼,国婚祭皇陵时磕得我头都肿了,最讨厌这套华而不实的繁文缛节。隐约觉得我不在的日子里未央宫确然发生过什么,而有人又在极力掩饰着不让我知晓。
我深深看了一眼旁边不知所措的程妈妈,似乎猜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我扶起她郑重说道,拿出手绢替她拭泪。
我在家里很少端起大小姐的架子,但只要我一端起架子,程妈妈也拿我没办法,虽然我是个不得宠的皇后,但是当时苏洵迎娶我入宫时,凤印也按照礼仪一并交到我手上,只要我手里有凤印,在很多重要事情上,都是可以过目的。
小菊抽抽噎噎道:“皇后娘娘有所不知,自从您去了金华殿之后,梅妃娘娘身边的枝绿便不断上门找麻烦,命膳房的人克扣油水,我们这些人地吃穿用度,都是程妈妈掏钱命人去宫外采办的,只要是我们宫里的人走出未央宫,就会遭到她们的围堵,弄坏我们的东西不说,还要被她们打骂,程妈妈曾为了我们去找枝绿讨个说法,她们便用滚汤故意泼伤,还说是我们自己莽撞不小心。”
小菊说着,边露出手腕,白皙的肌肤上,多了几道青青紫紫的淤痕,我心中“咯噔”一跳,不可置信地看着被层层白纱包裹住的双手,这样一双手,恐怕连照顾自己起居生活都有问题,这简直是宫廷霸凌。
我说:“我竟不知你们在未央宫过得是这种日子,为何不去金华殿找我?”
“奴婢们好几次想过去找皇后娘娘您,但是都被程妈妈拦下来了,程妈妈说皇后娘娘您刚入宫,根基不稳,很容易落人口实,让我们先暂时忍让,可是,可是······”
小菊一边哽咽一边断断续续地说着,后来说的话我也听不进去,只觉得愧对未央宫的所有人,同样为人之子女,父亲在我入宫前几天经常晚上独自坐在窗前发呆,有时瞧着瞧着我,眼眶就红了。
她们的父母是有多不容易才舍得自己的骨肉进宫为奴为婢,枝绿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也不该暴起伤人,她大可找我,找我总比找这些在宫里说不上什么话的宫娥们麻烦强,却又何必狠心牵连无辜,还连累程妈妈为我受伤。
说到底终归我也有责任,身为未央宫的主人,让其他宫人欺凌到自己头上,或许如果我不住在未央宫,她们也可以免遭此劫难。
眼下却不是自责的时候,她们既然在未央宫当值,便是未央宫的人,就算逞一时硬气,我绝无法放任楚黎的人任人欺凌,是时候上门到嘉庆宫捞一捞了,枝绿好大的胆子,一介他国人士,居然敢在大元的地盘,擅自做主欺凌我未央宫的人,未免太过分了些。
程妈妈用包裹着纱布的手掖了掖我,眼中神色复杂:“皇后娘娘,老奴知道您担忧众人,但是您目前人还在金华殿,请听老奴一句劝,眼下不是去嘉庆宫的时候,倘若事情闹大,圣上怪罪下来,别说我们,您也会因此遭受连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