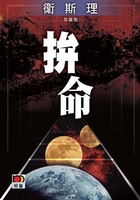太监们就不能一心一意督察她们了。隔岸观火,身上烤不热,看看火光怎样照红天空也好。太监们就此选定了对食的对象,目光锐利的便瞅准了“菜户”。“菜户”也是专供太监吃的,不是寻常人家吃食的门户。太监们衣食无虞,由里到外暖烘烘的,全不管宫女们为皇帝取露凉透了身子。他们选定了“对食”和“菜户”,纵然不敢违抗大太监的命令,给人家穿上衣服御寒,他们把蝇甩搭到脖子上,用两只手把人家身上捂热也好啊。他们割掉了“菜户”用不到的东西,把怜香惜玉的心肠也割掉了。宫女们不恨有病的皇帝,对健康的太监满腹哀怨。宫女的哀怨像草叶上的露水珠,太阳一晒就会消失,没有人再会从草根底下拾起来看看。一个朝代过去以后,女真人的后裔做了皇帝,在皇宫附近建起巨大的花园,园子里用青铜铸起宫女,托了盘子从天上取露,宫女穿了衣服,那也不是新朝的太监有了软心肠,担心宫女怕冷,而是新皇帝从老龙头长城外边的大山里过来,戴皮帽子,脖子上围野兽的尾巴,他们看了不穿衣服的宫女取露,到了有病的时候,再美妙的“仙方灵露饮”,喝进肚子里也会发凉,仙方失效。再过几百年改朝换代,无数不穿衣服的宫女,站在大大小小的城市街头宾馆院子里托了盘子,不从天上取露,却从头顶喷水,有的还蹲在台灯底下,光溜溜地闪亮,进入寻常百姓家里,那也不是老百姓全部过上了皇帝一样的日子,而是老龙头长城从西面打破口子,文化和大炮一起涌进来,与健康无关,离“仙方灵露饮”更不啻千里万里了。
可叹明皇帝熹宗连天上来的真的仙方灵露饮也喝不下去。他毫不怜惜三百宫女不穿衣服,从天上取露整夜挨冻,也不在意太监和宫女菜户对食,吃得很香,他没有食欲,不肯张嘴喝口仙露,连摇一下头都不肯了。大太监魏忠贤忧心如焚,守在床边,小太监轻手轻脚走进来,送给大太监一张图。大太监拿着图往后退,退到皇帝闭着眼睛看不见的柱子后边,把图展开,先看见了金笔题写的四个大字:九千岁祠。
大太监一看就不高兴了。金碧辉煌的大殿翘角飞檐,盘龙立柱,屋脊上蹲了六兽,都不能让他高兴起来。小太监猜不透,大太监九千九百岁为什么会不高兴,详细禀报,三河县送图的人说,打锣山矿主李百发不光为大太监修好了祠堂,还在祠堂里塑了像,大太监的塑像穿真金子做的衣服,金光闪闪可漂亮呢。大太监脸色铁青,不为所动,他打断小太监的话问对方,金子做的衣服会不会烂透。
小太监把蝇甩搭在一只胳膊上说,金子做的衣服永远不会烂。
大太监往皇帝躺的那面看一看,说:“衣服不烂有什么用?”
小太监头一低,说:“小的明白了。”
抬起头来把蝇甩一挥说:“小的叫他们给您老塑金像。”
血旺之兰
打锣山藏金丰富,只要大太监能活到小金驴重新回到金屋子里,拉着碾磙碾金豆子,就会有足够的金子给他塑像,连喝小孩脑子长不出的男根也一并塑出来,供于祠堂,让大太监九千九百岁绵绵不绝,成为后世用不完的财富。占据打锣山金矿的日本人则另有打算,他们造一座天皇金像,秘不示人,不管姚麻子如何费尽心机,想把天皇金像截下来,送给革命换饭吃。姚麻子脸上的麻子坑密密麻麻,想主意想得微微发红,用耙刺扎坏日本鬼子的汽车轮胎,打了一个胜仗,没有截到天皇金像。他腰间插枪,枕戈待旦,不睁眼梦中大战日本娘们,在涩儿腹中播下好运气的儿子,带人冲进打锣山金矿,仍然没有找到天皇金像。天皇已经投降,没有理由把自己的金像供在祠堂里,只能给革命吃了饭沤粪。打锣山的日本人仓皇逃命,他们不可能把金像带在身上。其实姚麻子仍然估计到,日本人会开着汽车逃窜,依然在路口上埋了扎汽车轮胎的大耙。农具武器照样好用,持枪的日本鬼子却不像原来那样能打仗了,他们不拼命,不用刀刺自己的肚子,简单地打一打,就举手投降了。开不动的汽车窝在坑子里,车厢里爬出日本女人,背上背着小枕头,也把两只手举起来。她们宽大的衣袖从高举的胳膊上往下滑,跟姚麻子梦里看见的不一样。姚麻子举枪瞄准,弄不准朝哪里射击,才能打不死人,只把扣子打开。大个的日本狼狗紧跟在女人身后蹿出来,一直扑向姚麻子举的枪,姚麻子赶紧搂火,子弹从狼狗的嘴里射进去,从耳朵后面穿出来,擦过日本女人的鬓发,飞到了看不见的地方。日本女人惊叫一声,鬓发蓬松,好像从来没有看见过打枪似的,是刚刚睡醒的样子。
果实丰硕诱人。不光是姚麻子想截下天皇金像,喜欢金子的人都想。打锣山的日本人用汽车载了女人,想从两座山夹起来的路口往北跑,跑到两千多年以前徐福带五百童男五百童女东渡求仙的渡口,再上船回国。有一支更大的部队在那里等候,准备伏击。大部队拿的枪没有旧的,哪一杆也比姚麻子腰间的那支亮,都是卡宾枪。他们可没有想到,有一支队伍拿着破枪,在前头截断,让他们等空了。他们气势汹汹地向南推进,放枪就像放鞭炮,弹壳像金子做的满天飞,他们毫不心疼。他们推进的速度不像预想的那样快,另一支大部队拿着跟他们一样的枪,把他们挡住,他们用子弹铺路,铺出一条金子一样的大道,仍然走不快。他们踩着自己人的尸体往前走,不等踩到敌人的尸体,又回到了原来出发的地方。打仗的双方操同一种语言,不像跟日本人打仗那样听不懂,只不过枪声大作太密集,说什么话谁也听不见罢了。战争结束以后,民夫老乡打扫战场抬尸体,凭脸色和模样,辨不出哪一些应该扔进大海里喂鱼,哪一些应该埋进墓地插一块木牌。有一些决定埋起来,就先放在空屋子里保存,等待挖坑,像一捆捆布匹一样垛放。坑子刚刚挖好,又认出了一些是狗杂种,为坏主子打仗,就连夜扔进大海,挖好的坑子留着埋自己人。
以打锣山日本人逃窜为开端,另一场战争打响,就再也没有改变过目标,就是占据打锣山,得到天皇金像。日本人只要没从海上把金像运回岛国,就一定藏在打锣山的洞子里。打锣山的金洞子纵横交错,幽深隐秘,个把金像藏在哪里,都会让人找不着。找不到天皇金像,打锣山也一定要争夺,它的深处蕴藏了那么多金子,想造什么人的金像都够用。战争就这样往下打。枪林弹雨,发生在三河县的战争都是为了向打锣山推进。由北往南打的战役结束不久,由南往北打的又开始了。战场在中流河上游,距于长河跟五表婶徐婉芝借钱给工人发工资挖金子的闺房不远。徐婉芝跟踪追探远行的男人,要看看男人的钢笔卡子被哪一个旅店老板娘换去了挽头发,结果丧失了勇气和信心,她看见的大山就在新的战场西边。那是片古战场,“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十字路口,自古过兵,通向四域,点起八方狼烟。路口高处是三河县的分水岭,下大雨,北边的路沟水向北流,南边的路沟水向南流。打仗的血也是如此流法。向北流的血穿过三河县城,流入打锣山,姚麻子备受鼓舞,他知道大部队又打了大胜仗,便命令推大磨女工快干。
打锣山改成了兵工厂,专为前方加工炸药了。革命固然还需要金子换饭吃,可是打仗比吃饭更重要,因为敌人要来夺饭碗。天皇金像可以暂时放在洞子里不找,要是找出来,敌人看见了会更加眼红。日本人留下来的发电机,为生产弹药照明,电线像蜘蛛网一样拉出去,吊在每一座支了碾磙子的小屋顶。兵工厂不使用日本人留下来的粉碎机粉碎火药,担心粉碎机肚子里的铁锤把火药敲响,炸碎了机器倒不要紧,就怕把金洞子炸塌,没法找天皇金像,也没法再挖金子。他们使用碾磙子碾药,用了工房子推大磨女工。推大磨女工抱着磨棍,推着大磨转圈。她们走惯了没有尽头的路,推着碾磙子转圈,走的路没有什么两样,很快也会习惯。姚麻子不带兵打仗,转到兵工厂指挥,腰间仍然带枪。
战事频仍,战场上血流成河,血旺的兰静如处子,鼻子倒不再流血了。金洞子小工宝元远行之后,兰把推大磨女工中最长的大辫子拢起来,梳成髻垂在脑后,再也没有梳过辫子。她每天早晨用宝元送给她的梳子梳头,想起金洞子小工把她的长头发像挽轳辘一样挽到胳膊上,她把自己一下子揪疼了,她也不后悔没让宝元早早碰她。她挽起髻来以后,头发不再能遮住的地方不如原来那么白,她也不担心,她相信远行归来的小工只要还回金洞子做工,仍然会像没有走的时候一样想摸她。金洞子上的小工不像念书人那样,衣袋里插两支钢笔,她也就不像闺房的女人那样,用丝线织一个小袋把男人的钢笔装起来。她需要在工房子里推着大磨转圈,没有闺房女人那么多闲工夫是一个原因,更要紧的是,她没有闺房女人那么多闲心想心事。说真的,金洞子上的小工没有钢笔要装,他也有差不多同样的东西,需要一个小袋装起来,他没有钢笔给人家写信,他可有笔给他自己画画。河滩上的婚礼没在地上烧香,兰让宝元把香烧在她的心口上,她就知道远行的小工香火炽盛,会把荒草烧成大火。她可不担心宝元会见庙就烧,宝元倒会有叩门的心思,可是人家庙门不开,他想烧也不成。宝元在她的门槛跟前长久徘徊,进不了大门,就是最好的例证。她当然知道,远行的路上会有自动打开的善门,等人往里走,可是宝元此番远行,志向远大,他要想找到更多的金线织衣服,就不会走到半路改变主意,走进荒门野庙里去。即便织衣服的金线太难找,单单为了他临走时候的懊恼,没有烂不掉的金线把兰缝上,他也该一个目标走下去,不看路旁的破门呱嗒呱嗒乱响。兰叫他放心远行不必惦记,郑重做出承诺,她将从心里挖出金线自己缝上,她真的做到了。
只有老天爷知道兰是多么困难。造人的老天爷既随心所欲,又刻意安排,他用一个模子造下男人和女人,偏偏给了兰那么旺盛的血。血旺的女人像饱满的果子,随时都会胀破,更会有被人碰破的危险。血旺的女人像雨季的河流浩浩荡荡,一不小心自己就会溢出堤岸。兰用大蒜贴脚心,用线绳勒****,用别人不需要用的法子止血,她的脚心快要被大蒜烧烂了,****差一点被线绳勒掉,她的血还是浩浩荡荡地涌流。她在河滩上送金洞子小工远行,滋润了青草,从此止住了鼻血,她的血其实还像原来一样旺,只不过不再流给人看罢了。她是颗饱满的果子,就永远汁液丰沛,她是条充盈的河流,就永远波涌浪翻,拍打堤岸。水草丰蕤的堤岸冲不垮,绝不是水流不汹涌,而是她自己用脚把大堤踩结实了,踩成了石头。兰的脚那么大,一双天足不缠裹,活泼快乐,不为“邻村通学”,只为了把自己心上的大堤踩紧,让河水流不出去,也不准别人随便来洗臭脚。宝元刚走那些天,兰把大辫子梳成髻,想起宝元找不到烂不掉的金线,那般苦恼,她觉得好笑,又觉得生气:远行的小工再不放心,也应该想一想,他在门口徘徊那么久,兰都没让他碰一碰门环。他要是不匆促远行,兰还会让他在门口苦等,兰的旺血自己由鼻子往外流。说实话,金洞子小工正是沾了远行的光,才早吃了饱满的果子。他到达了远行的终点,即便得不到织衣服的金线,他也该知足,不虚此行了。
随着河滩上的婚礼像一张褪色的画渐渐变旧,芦花飘白,兰才发现,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宝元刚刚新婚就远行,自有他不放心的理由。世界上所有的门,原来都有一个共同的原理。从来没有开过的门,总是紧紧地闭着,连主人也会忘记还有个门在那里,它自己不打开,外面的人自然再着急也没有办法。可是它一旦打开了,领略了外面的风光,再要关上,就不那么容易了。即便外面的人不用脚踢它,它自己也会呼哒呼哒摇动,想打开透一透风。更加奇怪的是,兰越是要紧紧地关门,用大脚把门顶住,用身体把门倚住,门越是晃动得厉害。外面没有风吹,她自己的身体把门晃动了。正是如此,兰最没有办法处置的,就是她自己的身体。河滩上的婚礼之前,她大流鼻血,她可以从流板顶上的大缸里撩了冷水洗额头,她可以用大蒜贴脚心,最没有办法的时候,还可以用线绳勒****,用窗纸裹了马粪堵鼻孔。现在她鼻血不流了,身体发颤,晃动大门,她不知道除了把门打开,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老天爷,你可真让人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