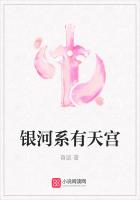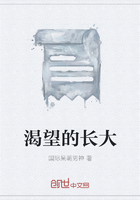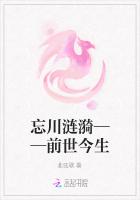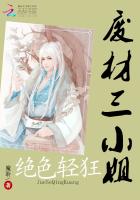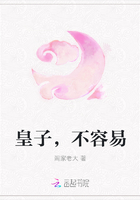孟子曰:“百里奚何尝有此事哉!考其初终,着于载籍,昭然无是事矣。夫欲相有为之君、进伯功之说,亦自有道焉。自鬻何事?而何为其然哉?此乃好事者极乎必不可为之事,以自文其陋也。以百里奚之事见于史册者考之,使奚生为秦人而不得仕,则此说犹可托也。乃百里奚,虞人也。生于虞,仕于虞,其在虞也,固与闻乎国政,而非因于草茅。即去虞也,犹为去国之大夫,而以羁抵禄。乃其不终于虞者即有故:晋献公思并虞,而其臣荀息献谋;以垂棘之璧、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因以并吞虞焉。于时外底外府之谋,昭然耳目;唇亡齿寒之祸,近在眉睫。虞公贪而不知,而其臣宫之奇谏。奇少长于君,言无足为轻重,晋人已先料之矣。而百里奚不谏,爱重其言,不如奇之自亵而无益也。此奚仕虞之事。于传有之,灼然可据者也。不谏而去矣,去乃之秦矣。其至于秦,而为穆公之所举,记载略焉,无所从考。乃即其去虞仕秦之初终而论之,则其必不为辱贱之行,固有可信而无容疑者矣。
“夫士之能有所为者,存乎其识量焉,存乎其志行焉。审乎可否之大辨而不迷者,智也;立乎远大之规模而有功者,贤也。惟自审也,乃能审时;惟自立也,乃能立功。而就自鬻之说,与奚之行事相并而论,反复思之,亦当相悬绝矣。
“以其识量言之:其不谏也,知虞公之不可谏也,贪人之迷也,而去之秦。当其时,年已七十矣。身世无几,而荣利有涯,尚何贪焉?乃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为污也,其贪而忘身,又一虞公也,可谓智乎?苟如好事者之言,则奚必不智而后可矣。而奚岂其然!不可谏而不谏,知利之足以污愚人而不可挽也,则贪夫苟且之情,昭然见其为不足与语,而可谓不智乎?不谏而必去,知虞公有取亡之道,不待其亡而先去之。虑不为亡国之俘,而不任亡国之咎,使其身可脱然于得失之外,以勿为当世所诽笑,是知爱其身也,不可谓不智也。奚之去也,当避患匆匆之际,似难择土而居;在无君皇皇之余,又疑难择主而事。乃于时,晋则内难将作,齐则霸业已衰,涉大河,越千里,而就秦于淠、渭以时举于秦。在穆公夙知其为虞之哲士而举之,奚遂知公为秦之令主而相之,度其可行,任大任而不辞,择之已审,不妄致身焉,可谓不智乎?合三端以论之,明于度身明,于度世;知衰年之易尽,非役志于宠荣;识当世之兴亡,但攸分于利义;则食牛之污,昏而不察,必无此理审矣。
“以其志行言之:志一身之富贵者,其行止于营图也;志一节之功名者,其行止于近小也。其为身谋也如是,则其为君谋也亦如是。在一国而何能及于天下?在一时而何能及于后世?利之所在,不问名也。乃奚之相秦也,通好于上国而上国尊之,策勋于天子而天子贺之,显着而名高矣;纪其事而《春秋》有王事之望,纪其言而《秦誓》列百篇之终,传闻为世法矣。若是者,岂与当世之贪利贪功,而一时非之,后世无闻,不以为耻者等?不贤而能为之乎?如或者之说,自鬻也,以苟自成其富贵也,而藉口曰吾有救时利国之策以成吾君也。此其为术,乃志行无聊、可羞而泣之事,乡党自好无所能成者且不可为,而谓以奚之贤,耻其君为小成之君,耻其身为小成之相,而肯为之乎?就所成而观之,无事不思大白于天下,无念不思昭对于后世,君荣而己不辱,亦惟己不辱而君乃荣。若夫志趋卑污,则所行不越于尺寸,小功虽立,天下且立待其倾覆,而为后世监,亦何足以测贤者立身之本末哉?”
故奚与穆公遇合之际,事虽不传,而大要去就皎然之大节,足以动穆公之旁求久矣。曰五羊之皮食牛者,或以奚食邑于五羖,而世称之日五毅大夫。曰自鬻者,或以奚为官奴之称,而古人命名以质,犹晋侯之名圉,莒子之名仆,而好事者因附会以成其说,皆不足深辨。独是贤者之出处光明正大,千古一辙,而生死以之,不可不务白也。
【心理穿梭】舜之处象,与周公之处管、蔡,其所以不同者,先儒论之详矣。然所谓“管、蔡之叛,忧在社稷,孽在臣民;象之欲杀舜,其事在舜之身”,此语亦须分别看,非谓一身小而社稷臣民大也。
使象恶得成,则天下且无舜,而昏垫之害谁与拯之!舜之一身所系固不轻,而以乱天下万世君臣兄弟之大伦者又岂细故!此处只论舜与周公所处之不同,更不论象与管、蔡罪之大小与事之利害。到兄弟之性,更以利害较大小,则已落私欲。若以罪之大小言,象之亲弑君亲,又岂可以祸不及于臣民为末减哉!
圣人之敦伦、尽性,只是为己,故舜于此且须丢抹下象之不仁,不商较其恶之浅深、害之臣细,而唯求吾心之仁。故象唯欲杀舜,则舜终不得怒而怨之。管、蔡唯欲危成王之社稷,故周公不得伸其兄弟之恩。以兄弟之恩视吾君宗社之存亡,则兄弟为私;以己身之利害视兄弟之恩,则己身为私。总为不可因己身故,而藏怒宿怨于兄弟,故不特不忍加诛,而且必封之。若其比肩事主而借兵端于我以毁王室,则虽未至有安危存亡之大故,而国法自不可屈。故孟子言瞽瞍杀人,而舜不得禁皋陶之执;若象以杀舜为事,事虽未遂,而弑械已成,其罪固浮于瞽瞍之杀人也远甚,藉使皋陶欲执之以抵罪,则舜必禁之矣。
虽云圣人大公无我,然到此处,亦须照顾自己先立于无憾之地,然后可以立情法之准。世儒不察,便谓圣人概将在己、在人作一视同等,无所分别,无所嫌忌,但以在彼善恶功罪之小大为弛张,而日此圣人之以天地为一体者也。为此说者,蔑差等以直情而径行,其与异端所云“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共命”一流荒诞无实之邪说又何以异!所以圣人言礼,必先说个别嫌明微,以为义尽仁至之效。若于所当避之嫌,一概将在己、在物看作一例,却向上面辨理之曲直、害之大小,即此便是人欲横行,迷失其心。
胡文定传《春秋》,谓孔子自序其绩,与齐桓等,为圣人以天自处,视万象异形而同体,亦是议论太高不切实处。使孔子视己之绩,如人之绩美词序之而无嫌,则舜可视象之杀己与天下之杀其兄者同,则又何待其害及于宗社臣民而始加诛哉!尧授天下于舜,则舜必让之。如但以社稷臣民为大,则安社稷、绥臣民者,宜莫如舜,胡不慨然自任,而必逡巡以逊邪!象之欲弑舜也,盖在舜未为天子之日,故小儒得以孽害之小大立说。向令舜已践帝位,象仍不悛,率有庳之不逞以图篡弑,岂不与管、察之流毒者同!将为舜者遂可俘之馘之以正其辜邪?使然,则汉文之于淮南,且但迁之而未尝加辟,然且“尺布、斗粟”之讥,千古以为惭德,然则使周公而身为天子,其不可加管、蔡以上刑亦明矣。
夫周公者,人臣也,不得以有其身者也。身不得有,故兄弟亦不得而有。兄弟之道,视乎身者也,非父母之比也。不得有身,斯不得有其兄弟;得有其身,则得有其兄弟矣。身所有之社稷,身所有之臣民,何患乎无君而又何患乎乱之不治,乃亏天伦以曲全之!是犹刳首以救肤,割肌以饱腹也,不亦慎乎!
“百姓如丧考妣,丧如字,谓以父母之服服之。四海遏密八音”,《书》有明文;“帅天下诸侯为尧三年丧”,孟子之释《书》又已分晓。古者民不得称百姓,至春秋时始通称之。古之言百姓者,皆赐氏而有姓者也。周则大夫世官而赐氏,夏、商以上,唯诸侯为有姓。“如丧考妣”者,即所谓“帅天下诸侯为尧三年丧”也。若氓黎之不得以父母之服服天子,自理一分殊、天理自然之节文,与诸侯之不得郊穑、庶子之不得丧其母、支子之不主祭一例。故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且礼也者,文称其质,物称其情者也。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知愚贤不肖之杂,即有君如尧,可以感其哀于仓卒,而必不能固其情于三年。民之质也,虽企及而必不逮者也。乃驱天下而服三年之保丧,无有斩衰菲屦,纵饮狂歌,以经舞而以杖斗者乎?则是乱礼丧真,而徒媒其君亲矣。故于礼无庶人服天子之文。其言“百姓”者,实诸侯也。汉文短臣子之丧,而反令庶人同制二十七日之服,薄于亲而厚于疏,乱上下之别,其悖甚矣。南轩以“天下臣民”为言,亦未可与言礼也。
“人君为不善,而天命去之”,于命言之,则非正命,于天言之则自正;于人之受命而言之,则非正,于天之命人而言则正。“惠迪吉,从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正天命之正也。南轩于此,辨得未精。舜、禹之相历年多,自是正;尧、舜之子不肖,自是不正。故朱子说“本是个不好底意思,被他转得好了”。总之,正不正,只可于受命者身上说,不可以之言天,天直是无正无不正也。
故乾之四德,到说“贞”处,却云“各正性命”,亦就人物言正。天地“不与圣人同忧”,本体上只有元亨,到见功于人物上,方有利不利、贞不贞。利贞于此者,或不利不贞于彼;利贞于彼者,或不利不贞于此:天下无必然之利,一定之贞也。
尧、舜与天合德,故于此看得通透。子之不肖而不传之,本不利而非正,却顺着天,用他所利所贞者,吾亦以之利而得其正,则所谓“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矣。
然此道唯施之子则可,若舜之于父母则不然。“号泣于吴天,于父母”,不受其不正也。舜之有父有子,皆命之非正者,特舜或顺天,或相天,一受之以正耳。
若桎梏死者,天命自正,受之不正也。唯天无正无不正,故曰“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有为有致,而后可以正不正言也,天岂然哉!
论舜、禹、益之避,集注“深谷可藏”四字大启争辨,自是立言不精。此岂避兵、避仇之比,且“南河之南”更有甚山谷如仇池、桃源也?
朱子抑云“礼之常也”,乃是定论。自尧以前,帝王亦皆传子,到尧时始有此君禅相摄之事。则三年丧毕,总己事终,自不得不避者,礼之常也。天下诸侯将迎推戴而出,自是奇特,非礼之所恒有;则亦舜、禹、益之所不谋。既必不冀望,亦不须防备。君有适嗣之可立,己亦有先君之显命,两者俱有可立之理,自无心于去留,一听之天人而已,何容心焉!想来,“有天下而不与”之心,亦如此则已纯乎天理而无可加矣。朱子却又深说一步,云“唯恐天下之不吾释,益则求仁而得仁”,则又成矫异。夫舜、禹岂求仁而不得仁乎?若必以天下之吾释为幸,向后坚卧不起,又谁能相强邪?
尧、舜禅授之说,愚于《尚书引义》中论之颇详,想来当时亦不甚作惊天动地看。唯其然,故益之避亦甚寻常,天下之不归益亦甚平淡。此处正可想古之圣贤廓然大公、物来顺应之妙。若谓“唯恐天下之不吾释”,则几与越王薰穴、仲子居於陵一样心胸。虽可以砥砺贪顽,而不足与于天理、人心之至。圣贤心迹,与莽、操、懿、裕天地悬隔,不但相反而已。欲知圣贤者,当以季札、子臧、汉高帝、宋孝宗、诸葛孔明、郭子仪一流作对证,拣出仁至义尽来,方有合处。
或问“朱、均不顺”一说,极为俗陋,罗长源作《路史》,似亦为此所惑。舜、禹当年是何等德业,朱、均虽不肖,固亦不得不服矣。刘裕心同懿、操,唯小有功于晋耳,然当其自立,晋恭帝且欣然命笔草诏,况圣人乎!有天下而为天子,不是小可事,云“不顺”者,乃似朱、均可以手揽而襟系之者然,真三家村学究见地也!上世无传国玺如汉元后之可执留者,不成朱、均介马孤立,大声疾呼以争于众曰“我欲为天子”邪?俗儒乐翘异以自鸣,亦不知量而已。
庆源“远而去,近而不去”之释,两“而”字下得不分明。此是通论圣人处。未仕之前,就之为近,不就为远;既仕之后,义不可留则去,道有可行则不去。倘作一串说,则不特孟子为敷衍骈赘之句,且既已远矣,盖未尝来,而何得言去?方其近也,且自立于可去、可不去之势,而亦何得遂定其不去邪?
吕氏说有命、无命处,极精当,正从孟子“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上体出,显义、命之异而后见其合。南轩云“礼义之所在,固命之所在”,虽与吕氏小异,然亦以见礼义之所不在,便命之所不至也。
新安错看“得之不得日有命”,将不得亦作命说。不知“命”字自与“理”“数”字不同,言命,则必天有以命之矣。故《中庸》注、录以差除、诰敕拟之。既不得矣,则是未尝命之也。
孔子曰“有命”者,谓我若当得卫卿,天自命之也。“得之不得日有命”者,言当其不得,则曰我若当得,则天自命我,而今未也。故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道则人有事焉,命则天有事焉之词。若不求,则不可以道言;不得,则不可以命言矣。
或疑孔子以道之将废为命,孟子抑曰“莫非命也”,则不必受命得位而后可以命言矣。乃孔子之言废者,则既得而复失之词。孟子之言“莫非命”者,则以言乎吉凶祸福之至,犹朝廷之一予一夺皆有诰敕以行其令也。唯吉凶祸福大改异处,故以天之有所予夺者而谓之命。若人所本无,因不予之,人所本有,因不夺之,君子于此,唯有可行之法而无可受之命,故谓之曰“俟”。俟者,未至之词也。藉当居平无得无丧之时,而莫不有命,则更何所俟哉?故生不可谓之命,而死则谓之命,以其无所夺、有所夺之异也;不得不可谓之命,而得则谓之命,以其无所予、有所予之异也。
若概乎予不予、夺不夺而皆曰命,则命直虚设之词,而天无主宰矣!君子之素位而行,若概乎生与死、得与不得而皆曰有命,则一切委诸大造之悠悠,而无行法尊生之道矣!且不得而亦言命,则是得为常。而不得为非常君子而以非常视不得也,又岂非据愿外以为固有、惊宠辱而生怨尤也哉!
天既生人以后,士则学,农则耕,天子之子则富贵,士庶之子则贫贱,日用饮食,一切寻常事,都不屑屑劳劳授之以命,而唯人之自为质。此天之所以大,而人之所以与能也。世俗不知,乃云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于是有啖鲐餐糕、破枕蹂花之诞说,以恣慵惰放逸者之自弃。使然,则立乎岩墙之下亦无不可,而其自云“知命”者,适以为诬命而已矣。是与于无命之甚者也,而况义乎!鉴于此,而后知吕氏立说之精。